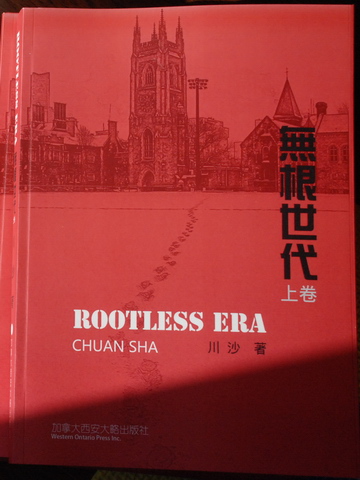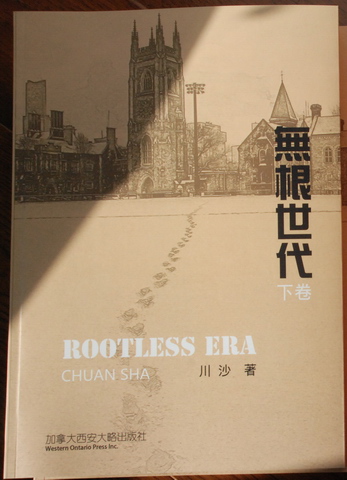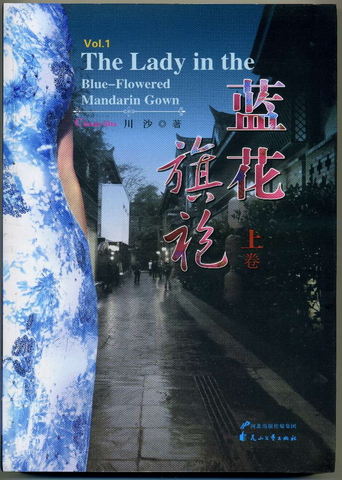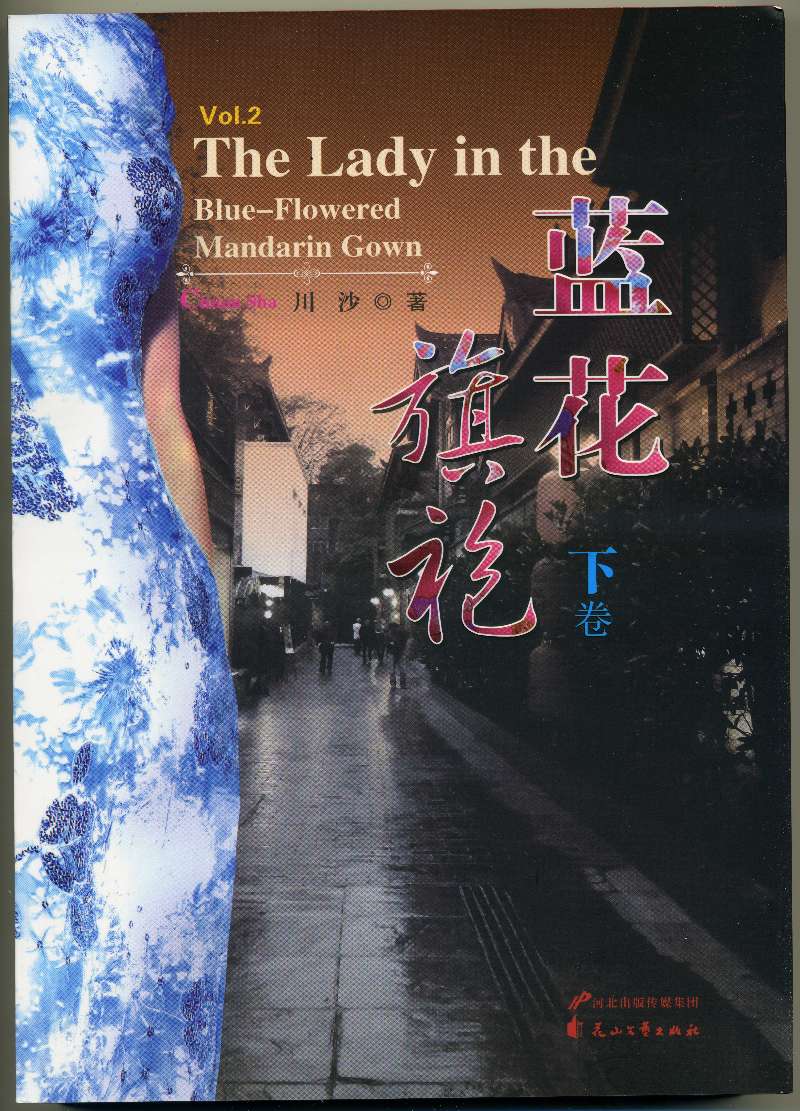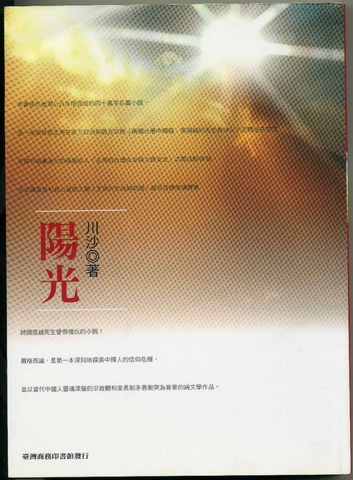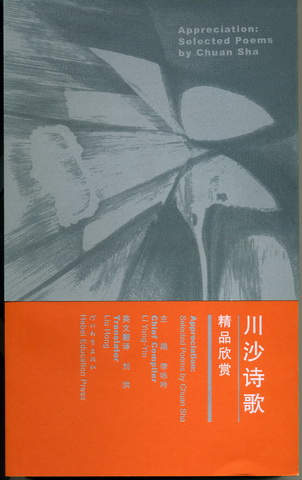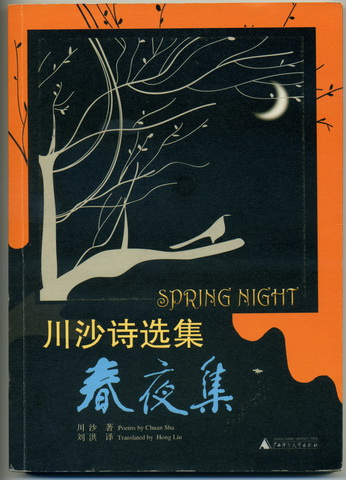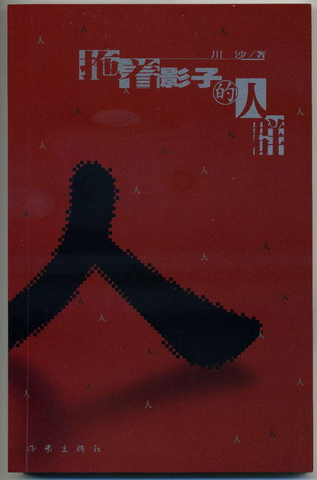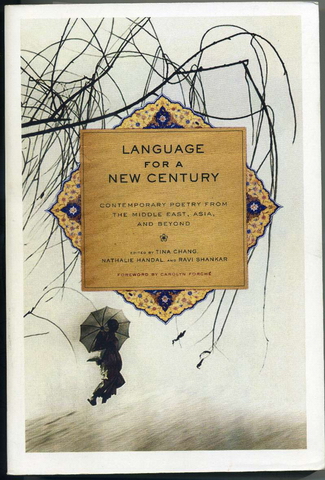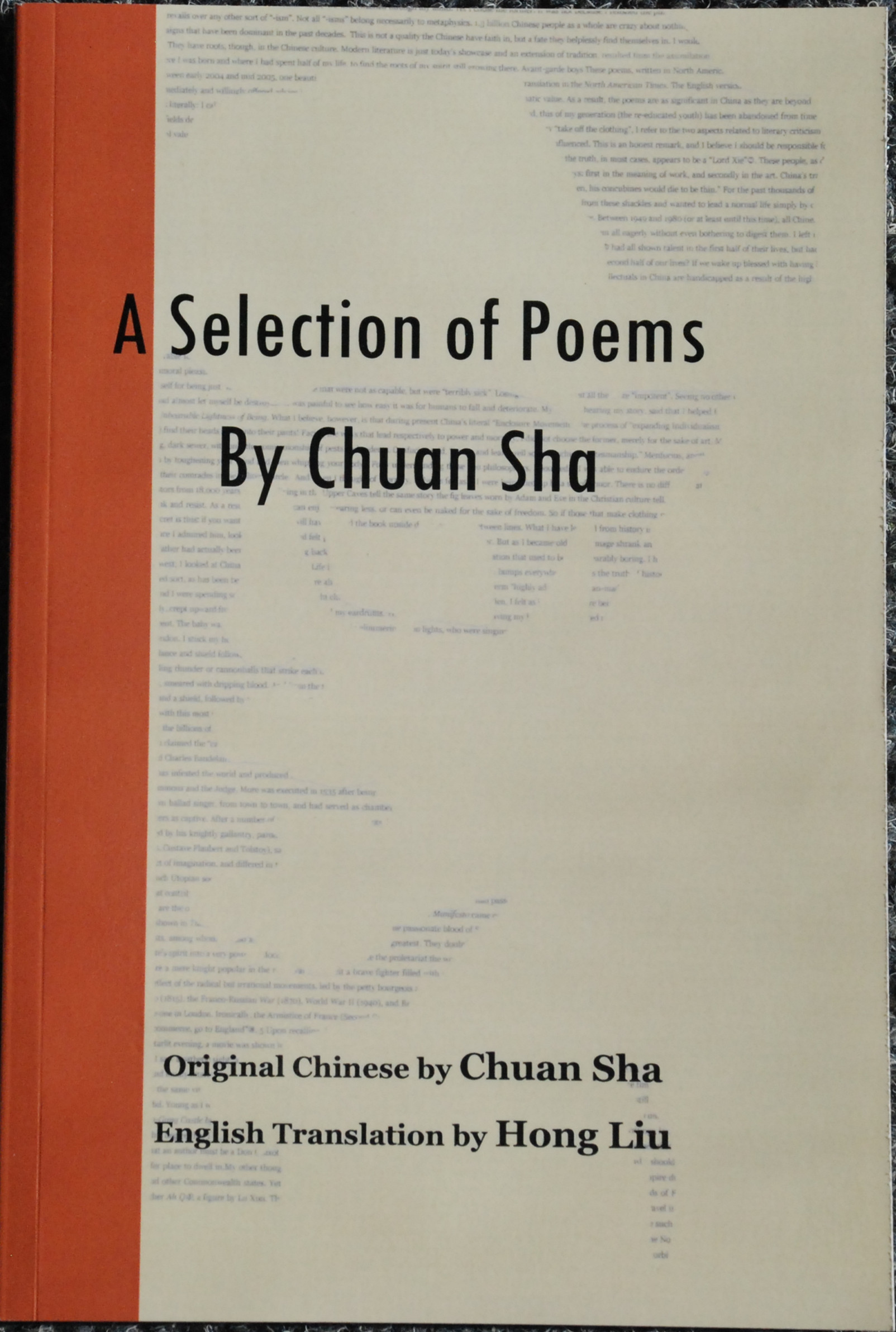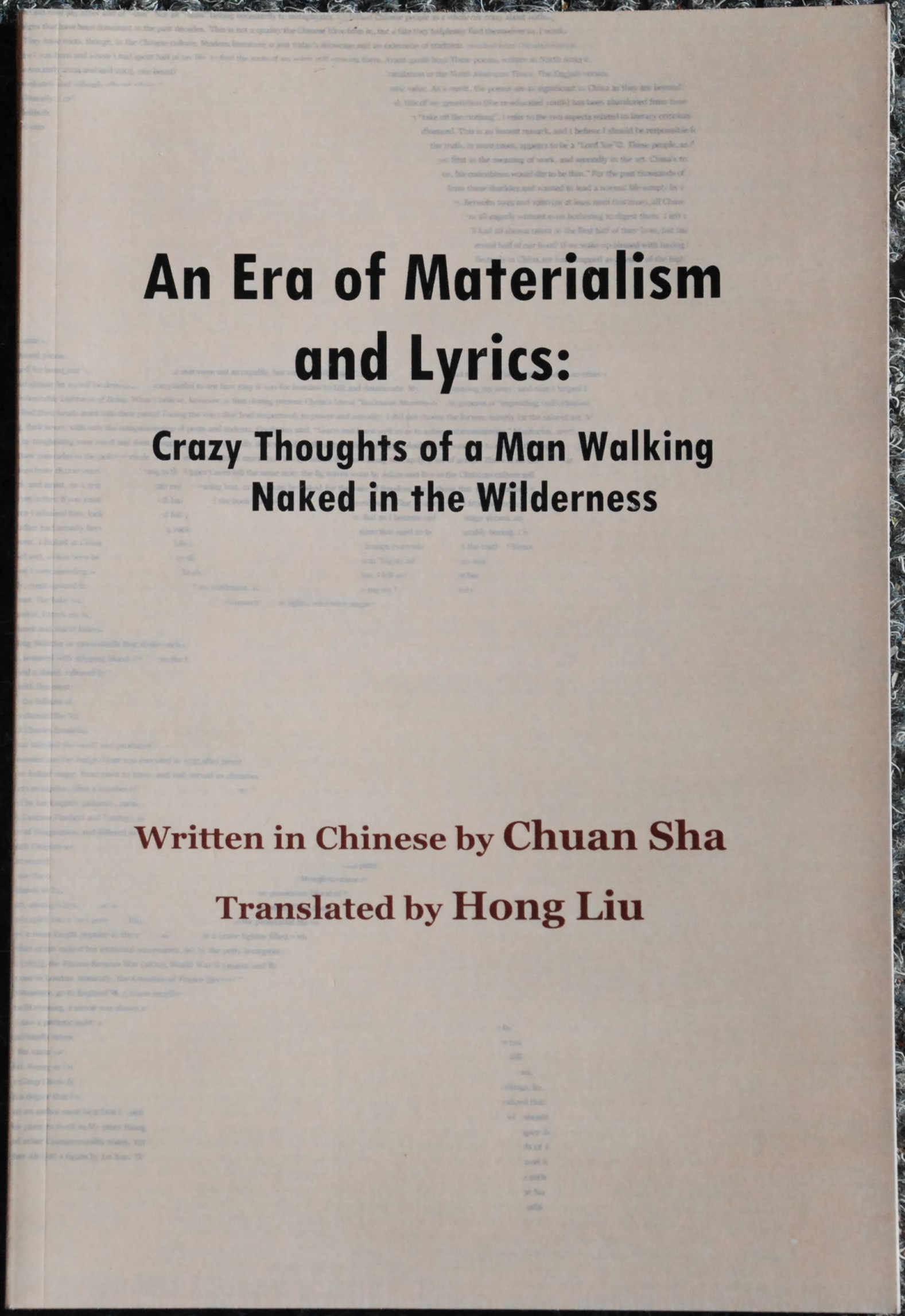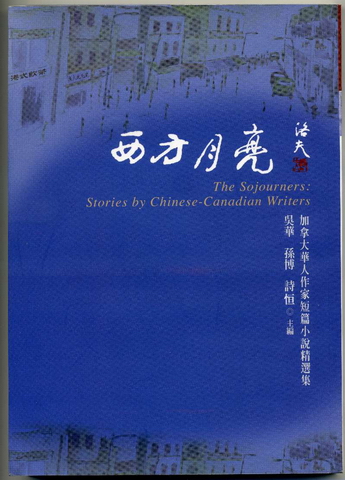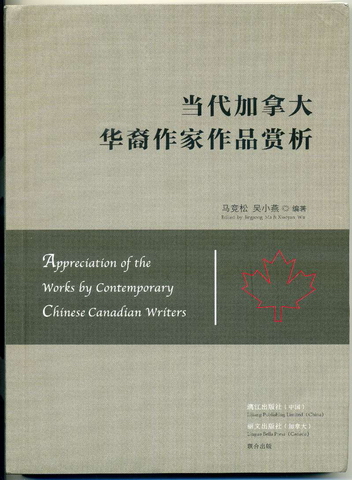(24)当年,母亲也是这般丰姿
当我在姹紫嫣红的花园里
两排摇曳着绿叶的冬青树间
铺着卵石的小道上
当我看着那身着夏裙的少妇
丰腴的身段
白皙如玉的肌肤
袒裸的手臂牵着那
满脸眷恋的
大脑袋的男孩
花瓣般的小手儿,
还有男孩那
步履蹒跚的憨姿
在这阳光融融的日子里
在这花儿吐露芳馨
彩蝶飘逸的夏日雨后
在这恬静怡人的伊甸园
呵!
那个年代
也是在一个姹紫嫣红的花园里
在两排摇曳着绿叶的冬青树间
在铺着卵石的小道上
在这花儿吐露芳馨
彩蝶飘逸的夏日雨后
也是这般伊甸园似的恬静怡人
当年
母亲也是这般丰姿。
(原载川沙诗选集《拖着影子的人群》)
24) Mother as Beautiful
I was taking a walk in a garden
Along a trail of cobbled lane
Lined by two rails of evergreen trees
When I saw a young woman in a summer skirt
Beautifully shaped
Marble white skin
Taking the little hands of
A big-headed boy who looked at his mother
With love
The boy walked slowly, clumsily
With endearing hesitation
Bright day when the sunshine poured down
Upon the fragrant flowers
After the rain butterflies danced around making
The garden Eden-like in peace
Oh, what a time
It was!
It was in a flowery garden
That a cobbled lane led to before
The evergreen trees nodding with leaves upward
The sun appeared after a summer shower
And shone on the fragrant flowers around which
Butterflies danced
Peaceful just like Eden
That year Mother was like that
Young and beautiful
(First published in The Shadowy Crowds)
[24]母爱的赞词,回环的魅力
余 闲
川沙的这首诗,触景生情,由此及彼,赞美母爱,感叹时光,并无过多隐喻象征,方法自是传统的,情感也并无特异之处。此诗的创新点,在于形式上回环的运用。
诗的最大特点是先抑后扬,然后猛然收住,宛如一幕戏剧。让我们来看原诗:
“当我在姹紫嫣红的花园里/两排摇曳着绿叶的冬青树间/铺着卵石的小道上”
其先是平平的叙述,寥寥数笔,勾勒出背景:姹紫嫣红的花园,绿叶的冬青,卵石的小道。这些平实的写景,营造出安静而平淡的氛围。诗人在其间静静踱步,内心渐渐和平自适,尘嚣俱净。诗人的心境铺垫好了,主角开始出场。戏剧就开始有了起伏。
“当我看着那身着夏裙的少妇/丰腴的身段/白皙如玉的肌肤/袒裸的手臂牵着那/满脸眷恋的/大脑袋的男孩/花瓣般的小手儿/还有男孩那/步履蹒跚的憨姿/”
就在这些清雅自然的景致之间,出现一位少妇,身段丰腴,肌肤如玉,这是女性之美,温婉而动人;手牵男孩,教他蹒跚学步,这是母性之美,慈爱而温暖。诗人落笔,都着眼于勾勒少妇与男孩的外在形象:肌肤、大脑袋、手臂。但通过精致的笔触,我们可以感觉到少妇的温柔娴静,男孩的稚气可掬,画面中充盈着爱的空气。
“在这阳光融融的日子里/在这花儿吐露芳馨/彩蝶飘逸的夏日雨后/在这恬静怡人的伊甸园”
这几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心里也随之掀起柔柔的波纹,目光从母子身上散开去,于是看见一派更温和的景致:阳光融融,彩蝶飘逸,恬静怡人。注意,对比一下最初的景物描写,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已不知不觉地加入了更多感情色彩。起初的“姹紫嫣红的花园”,纵然色彩丰富,但也毕竟只是实景,到了这里,已成为“恬静怡人的伊甸园”,渗透着浓浓的主观意味。而花儿的“芳馨”,彩蝶的“飘逸”,不也是实景在诗人脑海中的投影,并酝酿出更为芳醇的意象吗?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已从最初单纯的赏景,到了此刻的物我交融,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于是诗人浮想联翩,思接往昔,神游故土。第二节就在这种情绪中开始了。
“呵!/那个年代/也是在一个姹紫嫣红的花园里/在两排摇曳着绿叶的冬青树间/
在铺着卵石的小道上/在这花儿吐露芳馨/彩蝶飘逸的夏日雨后/也是这般伊甸园似的恬静怡人/当年/母亲也是这般丰姿。”
“呵!那个年代”,这里出现了唯一的标点,重重的感叹号。诗人一声长叹,从眼前之景,联想起另一个类似的场景,类似的季节,类似的氛围。这里的景物描写,重复了第一节,造成互文的效果。最后异峰突起,一声喟叹:“当年,母亲也是这般丰姿。”诗歌至此戛然而止,却是余音绕梁,让人陡然有种莫名的惆怅,却又道不出来。是怀念温馨的母爱?是悲叹母亲的逐渐衰老?或是站得更高一点,怅惘于时光的不可挽回,稍纵即逝?于是往昔就是此刻,此刻也是往昔。眼前的母子和美图,也正是自己所亲历的。时间仿佛悄然倒流,诗人在那个憨态可掬的男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满脸眷恋的大脑袋”,那“花瓣的小手”,那“步履蹒跚的憨姿”,都是自己曾拥有的。这一切都在母亲的保护之中,安全而平然,让人眷恋。而此刻呢?母亲在哪里?又有谁会来精心呵护自己呢?那时的母亲,风华正茂,美得入画,入诗,是诗人心中最美的图景,越过漫漫时空,触动诗人最美的忧伤。
这一节的开始与结尾,也是回环照应,营造出一种时空的苍茫感。
分析至此,再来回顾全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巧妙的布局。前面所有的铺垫,都是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到了最后来个揽辔收缰之式,丝丝缕缕尽入一握,顿时把全诗一下子拎了起来。而形式上两诗节的重复,与意境上的相互交融,达到了和谐统一。
此诗喜用长句,如“袒裸的手臂牵着那 / 满脸眷恋的/ 大脑袋的男孩/ 花瓣般的小手儿”,这样的句子,取消分行,当作散文来读,犹嫌拖沓蹩脚。但在诗句中,却营造出了一种悠长回旋的朗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