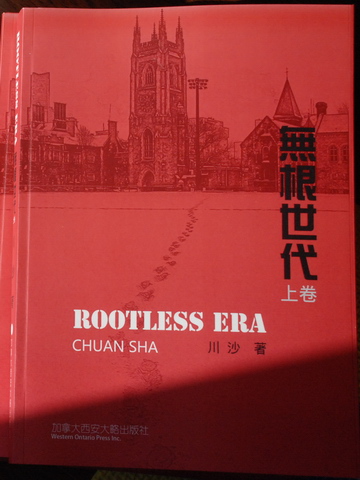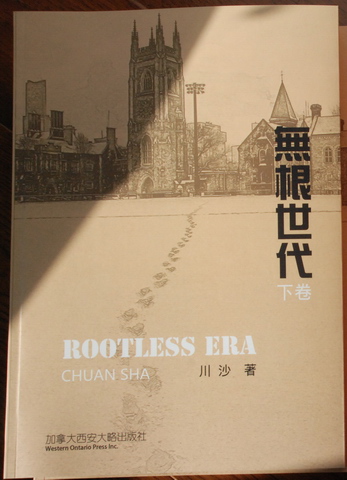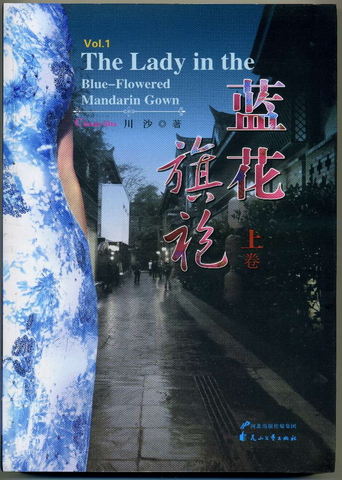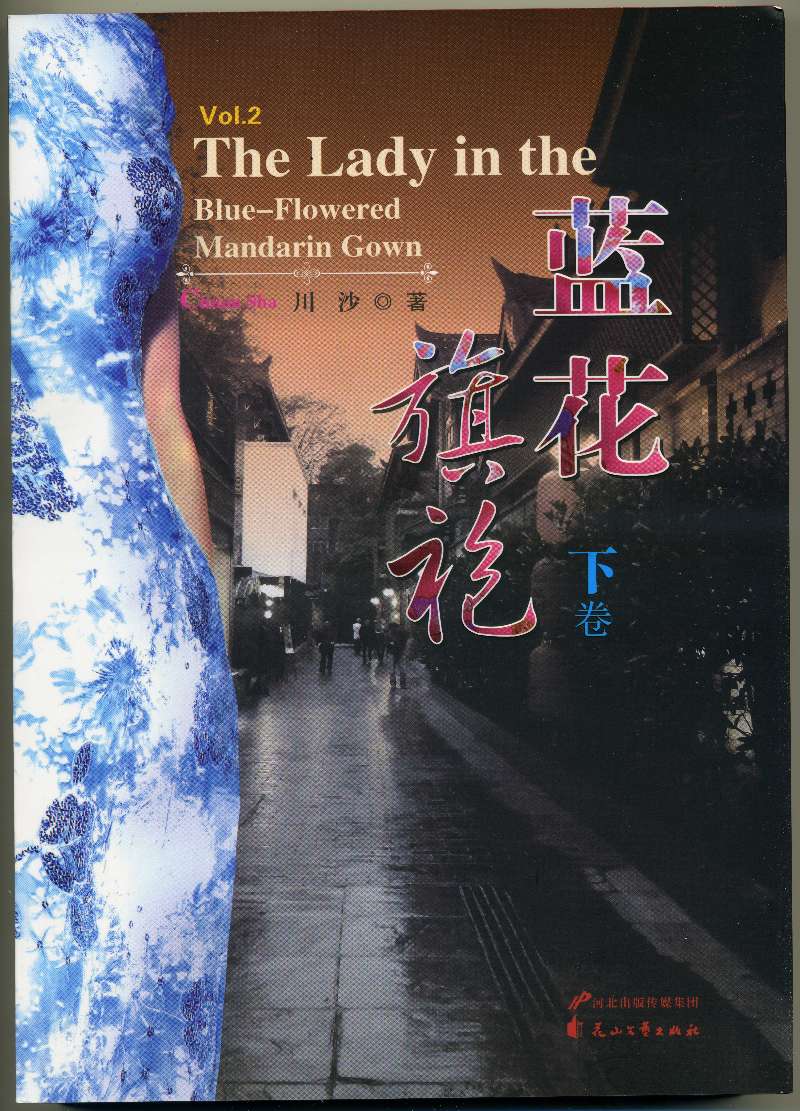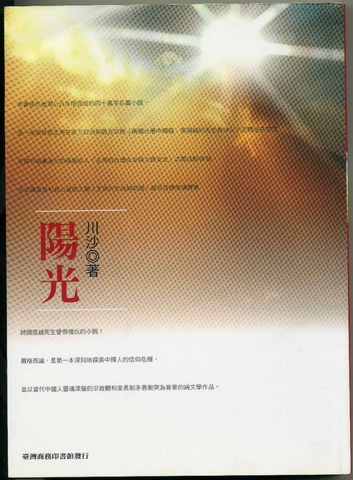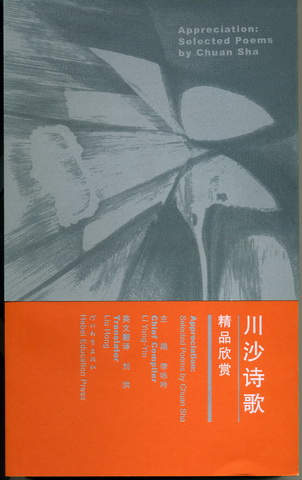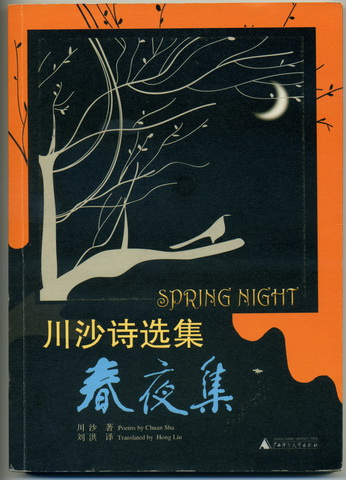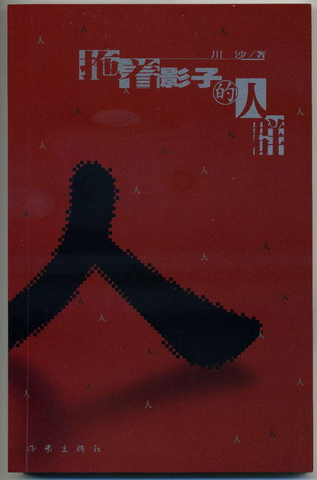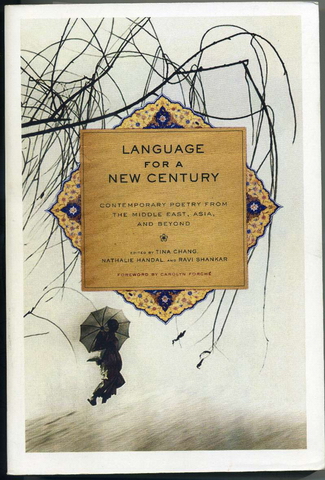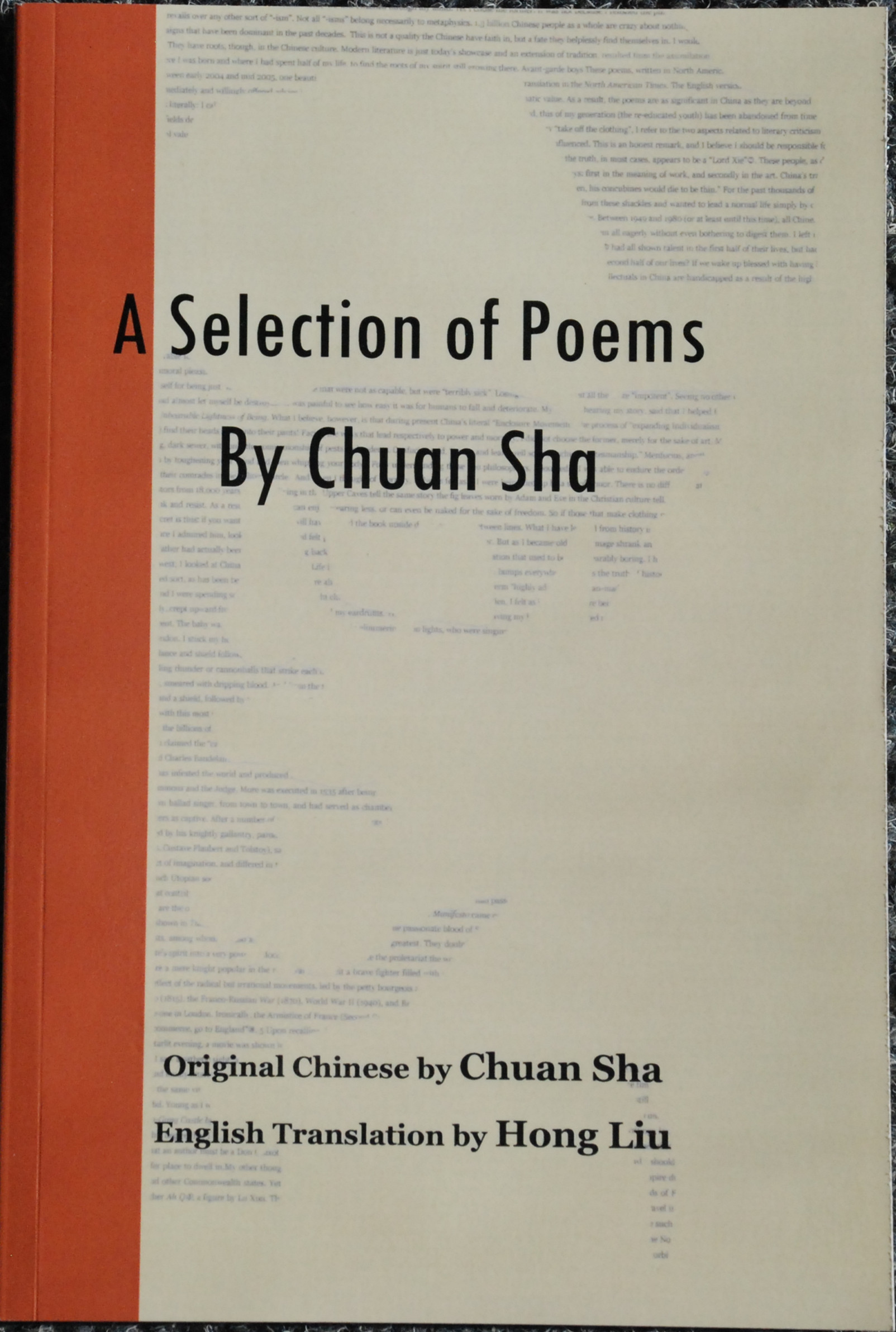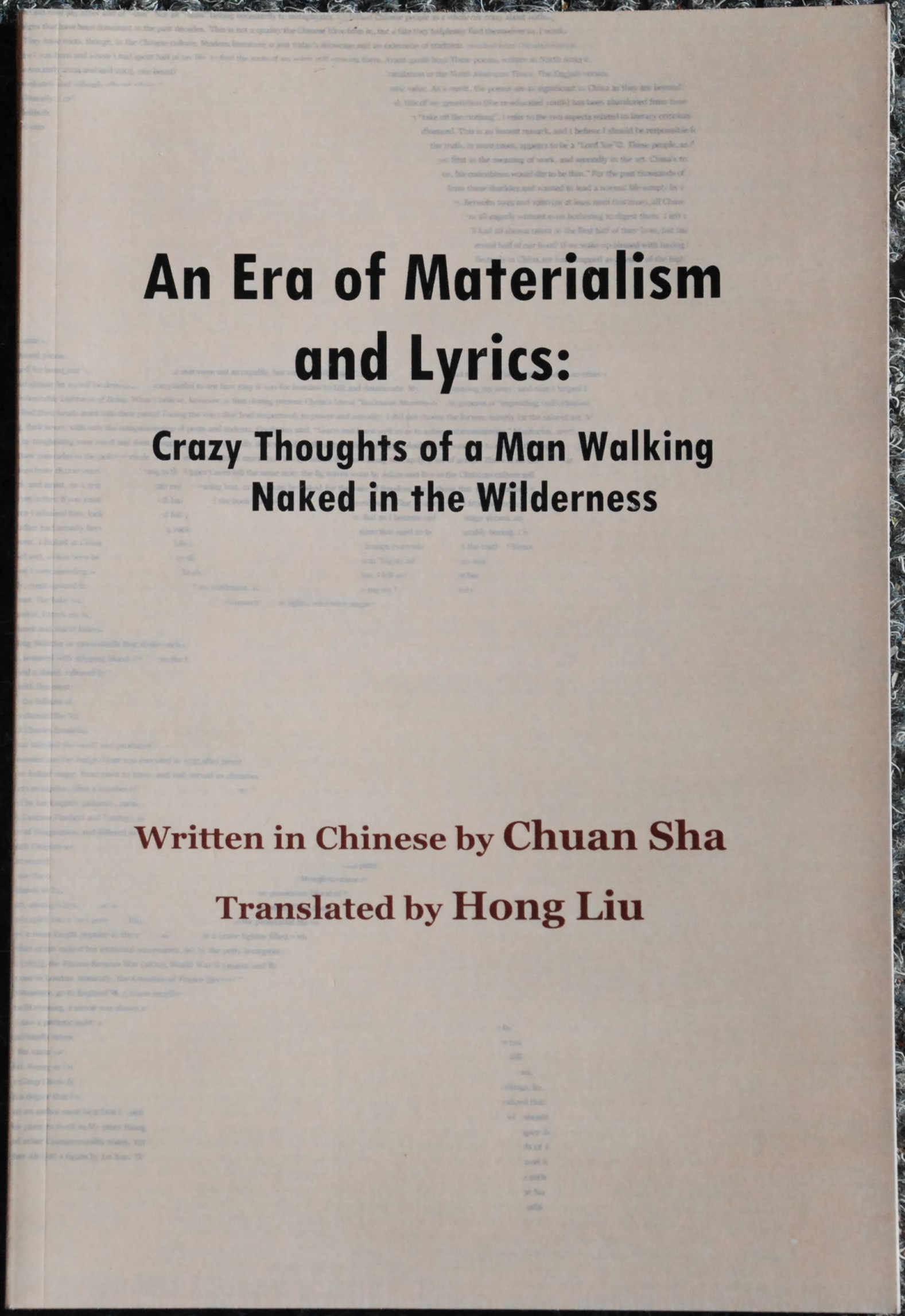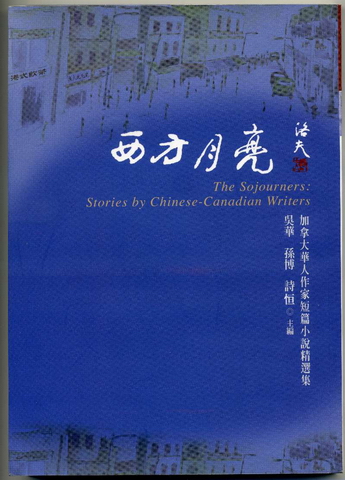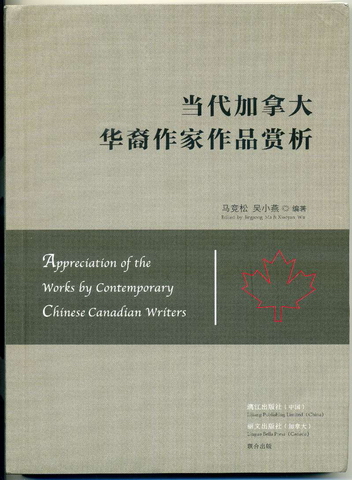四
斯坦因何许人也?
这里说几句题外话,我从小生活在重庆市的机关大院里,在我念书的小学,特别是我的同班同学里,很多都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过来的老干部,甚至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同船到法国留学的革命先驱的后代,在我生活的机关大院里,从小,我就看见过几个永远衣着朴素的“斯多葛”式纯精神至上的职业共产主义革命家,马克斯恩格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的精神食粮或宿命论,当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困难生活,或者他们本身的禁欲主义,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生活方式。即便生活在国民党陪都时期蒋介石宋美龄戴笠和许多军阀都生活过的《红楼梦》的大观园式的环境里,他们却在一年四季中,穿着浆洗得发白上面满是补丁的粗布中山服,脚下总是老式圆口布鞋,甚至在春夏秋季,在出入有苏联的伏尔加、波兰的华沙轿车代步的情况下,脚下仍旧穿着草鞋!
几十年后,我和小学时代的老同学翻洗老照片时,看见那些褪色了的黑白相片上呈现出来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衣服上那些大大小小的补丁时,真是感慨万千!
对比今天中国那些贪官污吏,那些每年都要枪毙判刑的一个个贪污上亿的共产党的败类,我为我的父母能够与共产党早期的那些精神至上者为伍,那些为了一种理想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为骄傲,我尊敬他们。
从斯坦因著作内很多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精神至上的探险家,一个置生死不顾的理想至上的知识分子。小时候,在我心目中的打虎英雄就是《水浒》里的武松了,后来到了英国后,从书里才看见,曾经确实有名有姓、有时间地点的,有过一个英国人在印度打老虎的事情,书里记叙了那个英国人只身在丛林里打死数十只老虎的事迹,才知道真正的打虎英雄,并不只是在虚构的中国小说里,而确实存在于现实的到印度探险的英国人中间。
从斯坦因在中国西北沙漠中那些照片上看,他总是行囊满身披挂,可以想象,里边不外乎是笔记本、钢笔、照相机、打火机、香烟(我不知道他是否吸烟,这里姑且猜测,否则,在那么疲劳的情况下,他怎么打起精神,喝茶和咖啡,在沙漠缺水的情况下,显然是不明智之举,也不是他那样的富有经验的探险家能够忽略的。)猎枪、手电筒、瑞士军刀、望远镜、指南针、罗盘、或许还有一小瓶苏格兰威士忌等等。想象他们在沙漠中骑在骆驼上,在朝霞和黎明之间穿行和跋涉,那些想象是很符合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男孩子罗曼蒂克未来世界想象空间的,当然,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之后,这样的想象,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尊敬,或许,即便他是一个敌手。
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记录的斯坦因辞条如下:
马克.欧雷尔.斯坦因爵士 (Stein,Sir Mark Aurel 1862-1943),英国人,原藉奥匈帝国,生于布达佩斯。早年在维也纳和德、英等国研究东方语言。1889-1899年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1900-1901年和1906-1908年两次奉印度英国政府令到我国新疆及甘肃搜寻古迹,1908年伙同伯希和在敦煌盗走中国大量文物。其中有唐朝的景教经典等。1932年企图再度来华,遭到中国文化界反对而作罢。其著作有《古代的和阗》(Ancient Khotan)(两卷,1907),《中国沙漠上的废墟》(Ruins of Desert Cathay)(两卷,1912),《塞林迪亚》(Serindia)(五卷,1921),《千佛洞》(The Thousand Buddhas)(1921),《埋藏在沙下的和阗遗迹》(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敦煌所发现的壁画目录》(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 Huang)(1931)和《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1922)(向达中译)等书。
说实在的,当我看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的向达译本,看见里边大量的关于斯坦因在探险途中那些相当数量的黑白照片时,内心里升起一种对他很深的敬佩的情愫。心里涌起一句粗话:“他X的,小子真棒!”,要知道,这是我对于自己服气的人最高的夸赞!作为一个探险家,毫无疑问,他非常勇敢和吃苦耐劳,绝对地具有牺牲和冒险精神。作为一种精神上提升勇气的“物件”,我将这本书随时带在身边,一直带到英国,我经常翻看这本书,特别长时间地凝视那些沙漠中他们艰苦作业、生活、生存的“实况”黑白照片,想象着他们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的所思所想所为,甚至浮想联翩自己什么时候也要这样去冒险一番,到一个什么世界上还没有开发的地方去艰苦地作为一番……
对于斯坦因,我的心情很复杂,虽然说,他是到中国盗宝,应该说是强盗,甚至是敌人,但是,他是一个值得我尊敬的“敌人”。这感觉就像看见大英博物馆那些保存完好的大量的中国文物一样,一方面是惊叹这些国宝级的中国文物没有腐烂在敦煌那个破败的莫高窟(斯坦因当年探险道敦煌的满清时期),而是被斯坦因带到了英国伦敦最好的博物馆里,被如此优质地保存和保护起来,这让我心里有感激之情。但是,反感的一面,自然是感觉到他们是到中国去偷运出来的,这样的行为,显然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那么,我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这样一件事情呢?我觉得,这就是历史吧!历史是客观的,对于斯坦因,应该向我们看待拿破仑、毛泽东这样的一些伟人,或者超能量级人物一样,后世之人,应该功过三七开地评介他们才更客观吧。
关于斯坦因,1987年夏天我在敦煌参观时,一本由宁强主编的《敦煌佛教艺术指南》上第一五0条“沙漠大盗-斯坦因”的辞条上记录如下:
继奥布鲁切夫之后,第二个来到敦煌藏经洞的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1862年出生于布达佩斯,在1900年至1930年间,曾四次到我国新疆、甘肃、内蒙等地考察,劫走了大量古代文书文物。1902年,他在“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听说了敦煌莫高窟的情况,就向往来敦煌。1906年斯坦因进行了第二次中亚考察,他于1907年离开楼兰,沿罗布泊南的丝路古道,穿越库姆塔格沙漠,经阳关跋涉二十余天于3月来到敦煌。当时正值王道士外出化缘,斯坦因耐心等待王道士归来。
5月,斯坦因来到莫高高,与归来的王道士进行谈判盗劫敦煌文书,王道士因官府有令封藏经洞,有所顾忌,斯坦因雇用一名翻译“蒋师爷”(蒋孝琬)由他出面表示愿意提供一笔慷慨的捐献帮助王道士修复庙宇;同时他发现王道士对玄奘十分敬佩,于是斯坦因就把自己打份成玄奘的热烈崇拜者,吹嘘说他是从遥远的印度来的信徒和追随者,负有把经卷送回原来的地方的使命,用这些鬼话打动了以卫道士自居的王道士,开始了肮脏的交易。王道士把一捆捆文书悄悄地运送给斯坦因,供他选择。斯坦因精心选择大量的文书和绣绘在绢纸上的绘画,整整装满了二十四大箱文书和五大箱绘画织绣,大摇大摆地运回了英国;付给王道士的仅是四十块马蹄银,即四十锭银元宝。王道士约定斯坦因要对这笔交易严守秘密,以保护自己,斯坦因当然乐意于此,王道士因此而表现得安详和满足。以至四个月以后,期坦因再次折回敦煌时,王道士又愉快地给了六百捆书稿。经过十六月斯坦因在敦煌盗劫的宝物平安运抵伦敦,收藏在大不列颠文部博物馆。斯坦因在敦煌盗宝的成功,竟使他在世界考古学界成了一位名人,并获得了英国政府的金质奖章。
斯坦因先后光临莫高窟五次。1914年他再次来到莫高窟,又用五百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搞到五箱手稿,大约四、五百卷。1930年,他还想再到中国盗宝,因中国学术界一致反对,才没有敢来。
斯坦因在敦煌盗劫三十多箱文物,有织绣品一百五十余方,绘画五百余幅,图书、经卷、印本、写本近七千余卷,加上他四次到新疆等地发掘出来的文物,数目巨大,可谓是一个“沙漠巨盗”。
中国古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关于斯坦因在敦煌盗宝,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将这些敦煌的文物当成我们人类的、或者说是地球的文物,而不是仅仅当做中国的文物来看,也许在若干年后,中国人,或者说人类,会因为当年斯坦因的行为而感谢他,就是说,感谢他将这些中国的宝物弄到了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恒温恒湿真空容器里好好滴保存下来,而不是让它们腐烂在敦煌莫高窟当时恶劣的环境中。或者说,让这些宝物毁灭在中国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手中。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会让一些人满意,甚至痛斥,但是,历史事实却毫不留情地证实了很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事情。一个例子是1949年国民党逃离中国去到台湾,将故宫博物院上万件的文物带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至今保存完好,而没有遭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风险,可以预见的有一天,国共两党都消失之后,在当时看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也许就是一件造福千秋万代的事情了。前两个月夏天,我在爱丁堡参观一年一度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时,看见露天舞台上一个个金发碧眼的西人上去一展歌喉,正遗憾没有亚洲同胞出现在舞台上时,突然来了几个日本人也上去引吭高歌,我心里的那种为亚洲人感觉到骄傲的心情是很难向人述说的。其实,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不喜欢日本人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而两国人民之间,有很多的友谊也是事实。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呢?因为相对于白种人,我们都是黄种人,是亚洲人。我自问自己,才发现,很多的情感是相对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而改变的。我在这里这样地说,无意要为斯坦因在中国的行为辩护,但是,看见那些珍藏在大英博物馆里德中国文物,我的的心情绝对不是那样的简单的。可以肯定的说,要是那些文物没有被斯坦因弄到英国,我们很难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试看今天中国报刊电视上经常报道的文物盗墓贼们干下的勾当,你就可以想象出更多糟糕的画面来,好在,这样的局面还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不至于泛滥,而在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那些敦煌的文物还能完好地保存到今天吗?
文中提及的奥布鲁切夫,即奥布鲁切夫.鄂登堡,他是俄国科学夫考察队成员,在其自著的《在中亚的偏僻之地》一书中记述了他于1905年在额济纳族黑城盗掘之后,又赶到敦煌藏经洞,用少许日用品为诱饵。从王道士手中换取几大捆内有珍贵的汉、藏、楚、突厥等文字的文书和部分绢画。他后来在1914年至1915年间,又从王道士手里弄去一大批文书,其中包括大量的汉、回鹘文写本和彩色塑像及绢画。同时绘制了共443个窟的平面图,拍摄了两千多张照片,存放在圣彼得堡冬宫亚细亚部,后为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其数量达一万二千多件,在1963年到1967年出版的《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一、二卷中公布了让全世界的学术界为之震惊前苏联所藏的敦煌文书。
沙俄的奥布切夫,鄂登堡是在斯坦因之前到敦煌盗宝,而在斯坦因之后又有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兰登.华尔纳,以及来自西伯利亚的暴徒的白俄匪军都在那儿大肆的盗窃和洗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