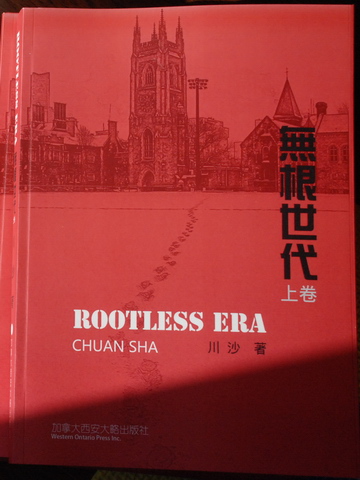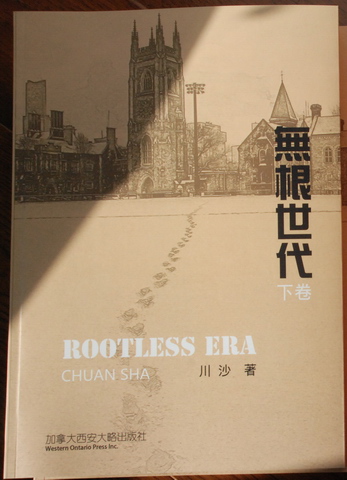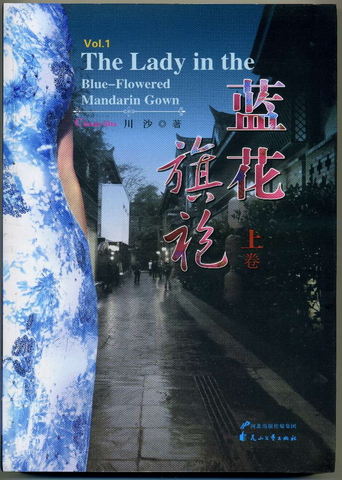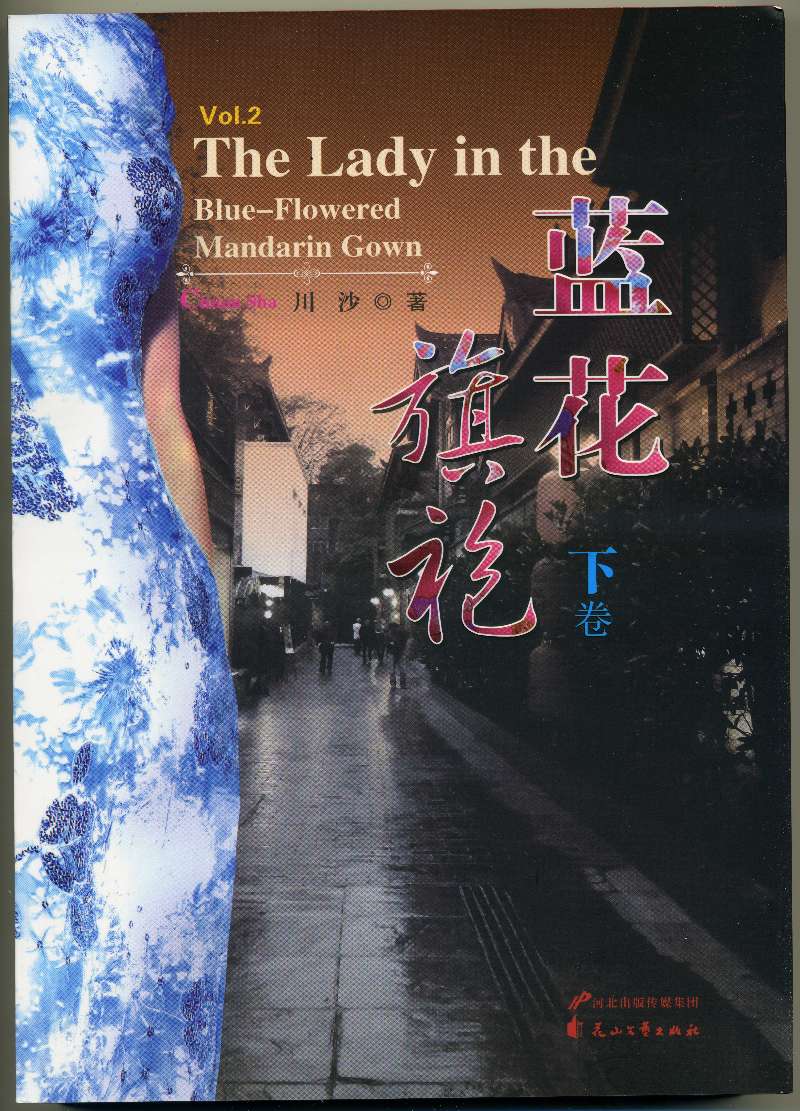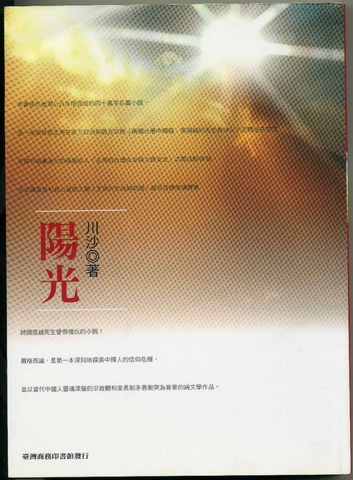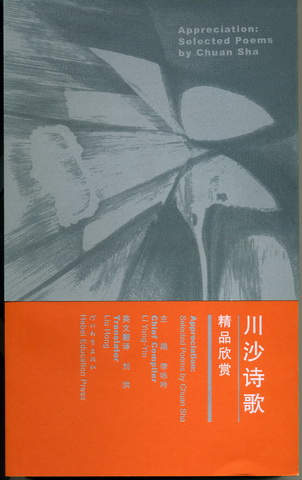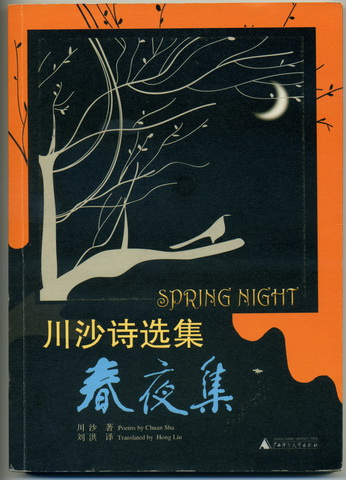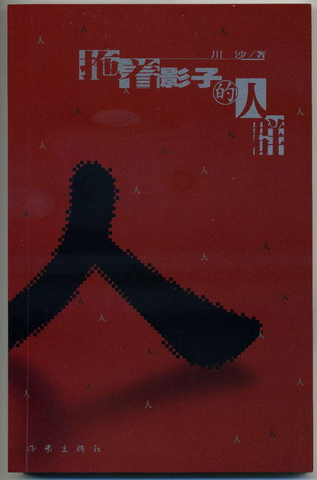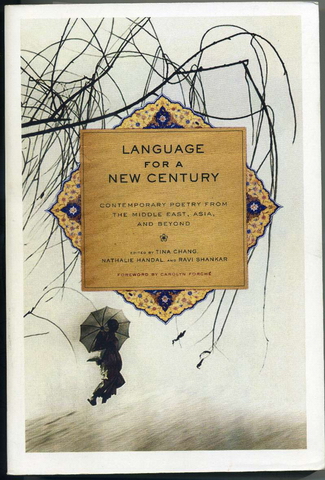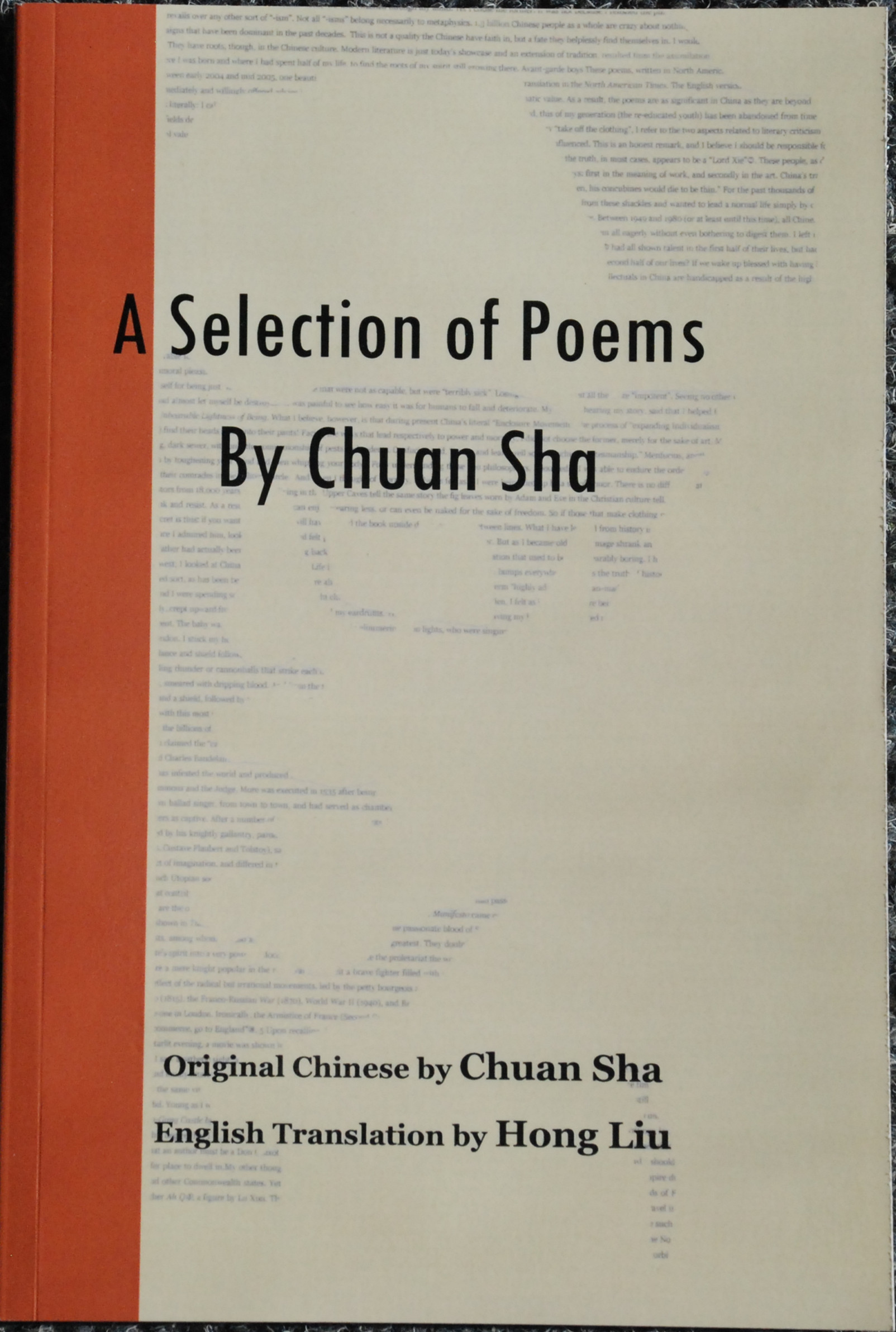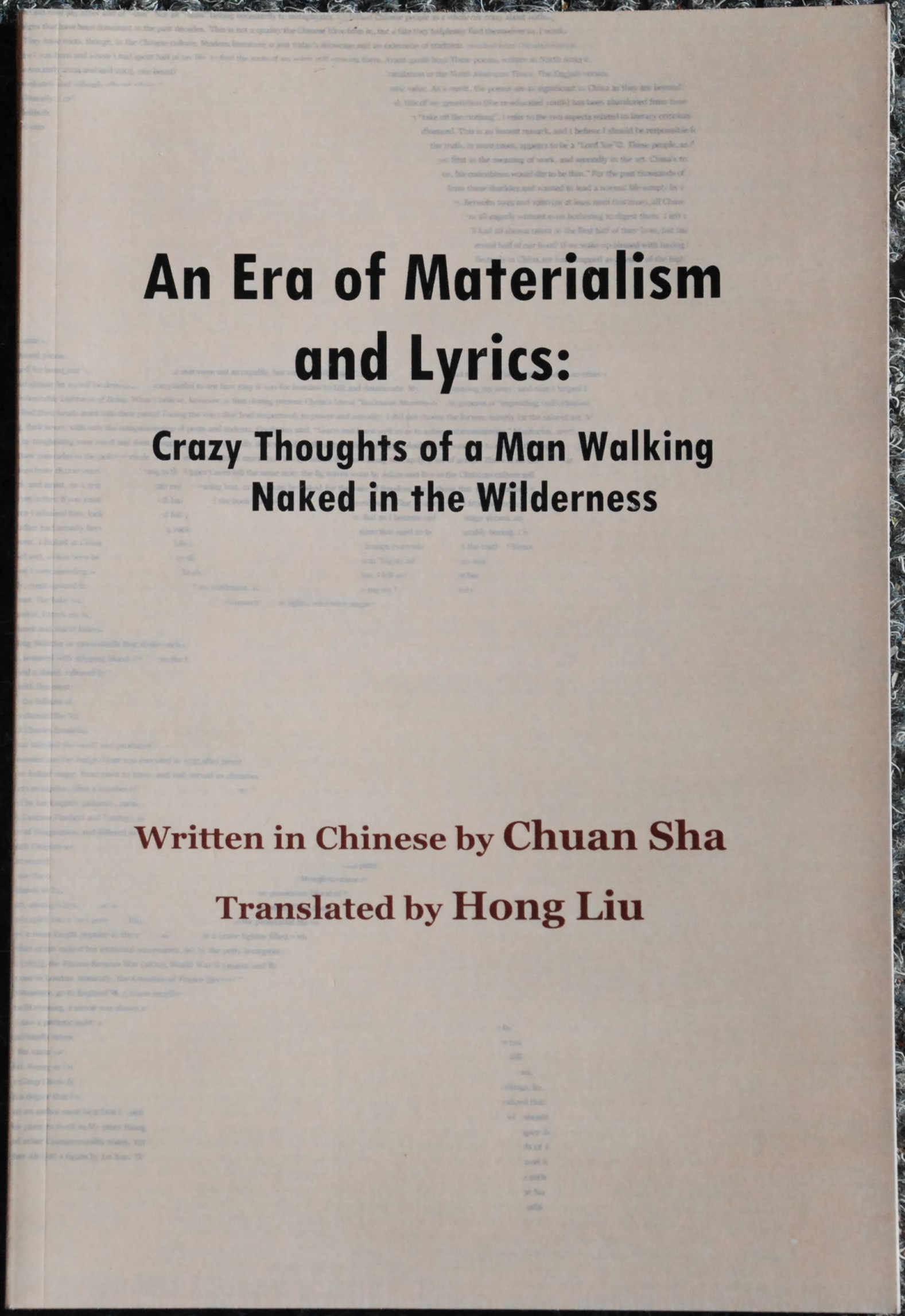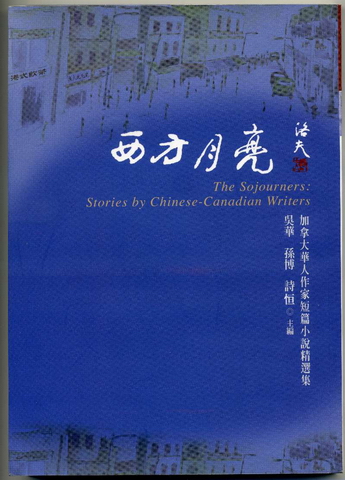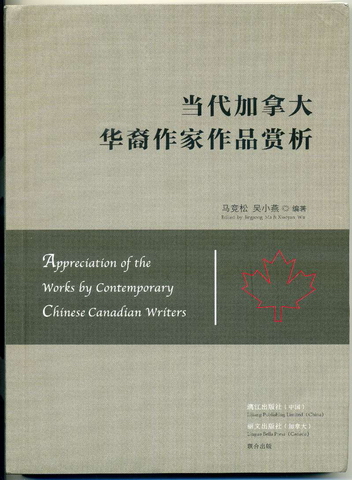三
到敦煌去“朝拜”一番,早已是我心里多年的宿愿。
1987年夏天,到新疆乌鲁木齐开会时,我满足了自己的愿望。本来,我出行的路线可以乘火车由重庆市到成都后,直接乘飞机飞乌鲁木齐,因为,那时已经有成都直飞乌鲁木齐的波音747等大飞机。但是,我却选择了重庆、成都、西安、兰州、嘉峪关、敦煌、乌鲁木齐这样乘安-24小飞机、巴士汽车以及火车这样的旅行路线。作为出版社编辑,带着组稿和参加会议的任务,如,参加在西安外语学院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和《读者文摘》编辑部主编郑元绪、副主编彭长城会面,到敦煌研究院会见段文杰院长洽谈出版事宜,到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参加“新疆外国文学学会成立大会”等任务,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条路线。至今还记得的事情是,乘坐只能载运20余人的安2型飞机飞越秦岭,遨游在“华夏文明的龙脉”森林的绿色海洋上,擦着山头的树梢起伏低飞,同时在小飞机上颠簸和呕吐的难受和快感……
在万里长城的最西端,开始领悟这河西第一隘口,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关隘,或者素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嘉峪关,品味和理解当年林则徐在诗句“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潸”里的悲凉(林则徐《出嘉峪关感赋》),感叹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种在清晨微雨,尘土不扬,柳色初绿的景色中的送别绝唱。在那里,我才第一次听说了“关外”这个字眼,就是说,嘉峪关和远隔万里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遥相呼应,我们内地叫关内,之外叫关外。在那里,我惊叹于嘉峪关西长城的古朴雄浑,肃然起敬在飞将军李广纪念碑前。
作为一次“长途旅行”,我做了专门的准备,提前出发,特别留出了在敦煌停留考察的一段时间。从南方湿润的重庆市第一次到干燥的中国西北,眼里的一切都很新鲜,除开沙漠、骆驼、西北嘉峪关长城,和一瓶汽水的价格就可以买一个大西瓜外,敦煌的壁画更是令我惊讶无比。说实在的,在敦煌莫高窟里看见的那些在窟壁上的壁画,如果是在南方的任何一个地方,由于潮湿的原因,不要说留存上千年,恐怕几个月都难以保存。所以,我觉得,敦煌那个地方,从地理上,对于物品的长期保存,是一个绝对的“风水宝地”。另外,敦煌文化,也因为地理上的原因,显得格外的特别。19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文学为什么特别灿烂,我觉得,跟俄罗斯位于东西方地理和文化之间,是有很大关系的,而敦煌的情况也很类似。
在古代,敦煌处于中国与西方诸国文化交汇的位置,因此,这个地理上的优势,促进了它艺术的繁荣。唐代敦煌壁画则是一个集中体现了敦煌艺术的精髓。特点是紧紧围绕宗教宣扬题材,用唐代特有的风格特点来描绘唐代佛教的主流信仰。敦煌壁画的内容、题材、风格特点、空间构造、线描特点、用色特点都表现着唐代佛教。其中的经变画、佛像画、和供养人画像等,其风格特征大都是直接对当时人物进行写生,并且十分注意个性的刻画,山水的风格特征则是体现在青绿山水的表现,并且在平面的画面中,描绘出接近三度空间的特有的图像结构。其中的“柳叶描”、“蚂蝗描”,用色则多表现在红、蓝、绿、棕、白矿物质颜料的运用。我特别注意那些壁画的颜料,因为,要保存上千年而不变色,绘画颜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询问了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员,据他们讲,当时用的大部分颜料大多都是矿物制的,还有一部分是从西域运来的,所以现存的西夏时壁画都特蓝特绿,那都是用蓝绿宝石研制的,历时千年经久不会变颜色,时间越久越鲜艳。那些颜料制作水平说明:中国早在1600多年前,就已经具备了很高的颜料发明制作技能和化学工艺技术,表明自那时起,中国的颜料制作技术及水平已居世界领先; 敦煌壁画的用色大多以红、黄、绿、蓝、白、黑、褐为主,色彩绚丽、细致、浓重、浑厚,形成了唐代重彩风格,也形成了中国重彩工笔画特有的美学审美观和艺术风格。
敦煌的莫高窟和榆林窟同属敦煌石窟艺术体系,两处石窟共保存有多个朝代的777个洞窟,约50,000㎡壁画和2500多身彩塑像。我认为,敦煌是研究中国美术史、音乐舞蹈史、服饰、少数民族文字、古代科技等研究工作者应该去朝拜的地方。
在敦煌期间,有两件事情很出乎我的意料,一件事情就是发现那里外国人特别多,比中国前去参观的人还要多,中国人里有些艺术家、特别是美术学院去临摹的学生特别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北京和南京佛学院的学生也很多,但是,他们中间有的学生虽然剃光头,但是,却穿现代T恤,戴棒球帽,并且饮酒作乐,和我们一样谈论美味佳肴、漂亮女人和市井红尘那些上不得书的男女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