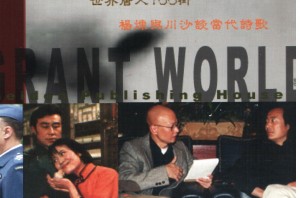哈博芳谈诗
——楊煉與川沙談當代詩歌
錄音整理:言 行 周 昕
攝影:畢建宏
(原載加拿大《移民世界》雜誌總第一、二、三期)
編者按:2001年10月21日至25日期間,國際著名旅英中國詩人楊煉應加拿大哈博芳讀書會(Harbourfront Reading Series)的邀請,由倫敦飛抵多倫多作當代詩歌演講和答辯,並應加拿大華裔詩人川沙先生及加拿大海龍出版社社長羅珈女士之邀,參加了出版社爲他舉行的招待會。在招待會上,楊煉先生受到衆多詩歌愛好者的熱情提問。同時,楊煉與川沙就當代詩歌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對話和交流。 1980年代初,楊煉在中國以《半坡》、《敦煌》等“尋根”詩震動了中國文壇,並以他的介乎於“朦朧詩”和“第三代”之間的“尋根詩潮”影響乃至催生了“整體主義”和“傳統主義”詩歌,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壇的地位。楊煉作爲當時的文化尋根潮中影響最大、成就最高的詩人,使他的名字成爲該詩潮的代名詞。1999年,楊煉獲得義大利的弗拉亞偌(Flaiano)詩歌獎,在這項詩歌獎的歷年獲獎者名單中,有愛爾蘭的希內和聖盧西亞的奧爾科特兩位偌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也有法國的博那伏瓦、捷克的赫魯伯和美國的弗林傑迪等當代國際詩壇最重要的詩人。這裏是楊煉與川沙就當代詩歌的一些經過整理的錄音談話,由於原文較長,我們將在《環球文壇》這個欄目裏分次予以陸續刊出,以饗讀者。
時間:2001年10月23日下午
地點:加拿大多倫多Westin Harbour Castle & Conference Centre 底樓咖啡廳
人物:楊 煉 國際著名旅英中國詩人 ,1999年義大利弗拉亞偌(Flaiano)詩歌獎獲得者,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者(以下簡稱“楊”)
川 沙 加拿大華人作家、詩人,有小說、詩歌在海內外發表和出版,加拿大華語詩人協會會長(以下簡稱“川”)
简 目
(一)春水西流——海外流散诗人
(二)群雄逐鹿——诗歌流派漫谈
(三)比“日日新”还新,比“后派”还后——杨炼诗歌简论
(四)零上还是零下?究竟什么是诗歌?
(五)巫师和政治——诗人的预见性和社会责任感
(六)國際玩笑——文学大于政治吗?政治可以杀人!
(七)批判、批判、大批判!——《十作家批判书》还是《十批判书》?
(八)《詩,自我懷疑的形式》,賦、駢、絕、律——杨炼回归先秦
(九)英语和爱尔兰语,白话与文言文——你不得不亲吻征服你的语言大棒!
(十)《中文之內》和《當代漢語詩人面臨的問題》——白话文有出路吗?
(一)春水西流——海外诗人
川: 楊煉,加拿大多倫多哈博芳讀書會每年的這個時候都會邀請二十來個世界第一流的作家來這裏演講,去年我有幸在這兒會見了一些朋友,例如北島、哈金,還有去年三月單獨受邀從美國轉道而來的莫言等,其中一些是多年未見面了的朋友。在這個異國他鄉的地方反倒把我們聚到一塊兒,很是讓人高興。此次受邀的近三十個作家裏面,你是目錄上面唯一的一張亞洲人面孔,我想聽聽你此行的感覺,還有這十來年你的情況及對當代文學的一些思考。
楊: 我在國外呆了很長的時間,我覺得,參加各種類型的文學活動、藝術節等等以及什麽的太多啦……這次我從倫敦飛出來,先飛到悉尼,然後到奧克蘭,然後又轉到了這兒。這種國際文學活動當然很有意思,因爲你可以跟雖然不同語言的,但是在同一個領域裏寫作的人們接觸和比較,這種比較,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特別是不同的地方,對我來說始終還是很有興趣。 尤其作爲使用中文的詩人。雖然,我現在可以用英文進行交流,但是,事實上,那個真正的我仍然隱身在中文的語言之內。一方面我盡可能的用英文進行交流,討論和闡述我對文學的看法、對生存的態度以及我的作品。但是,另一方面,那個隱身的我又面臨著一種無言的焦慮和痛苦。因此,在這兩者之間,在交流和不交流,說出和說不出,存在和不存在,一個活生生的詩人和一些看不見的詩之間,某種反差始終讓我有興趣 。實際上這也構成了一種能量。讓我的寫作、或者說我對中文的理解不斷地被逆向地加深。當然,哈博芳是一個有名的藝術節 ,來的作家都是些著名的作家,其中一些我在其他的藝術節,詩歌節上也見過,那麽,對於我來說最有興趣的是,把我感到的這種區別,在某種意義上,也轉述給他們。
川: 你目前是居住在英國?
楊: 倫敦。
川: 88年剛出國時,你好像是在新西蘭?
楊: 我待的地方多啦!新西蘭,澳大利亞,美國,德國,現在在英國。這個地方待的時間比較長。
川: 95年我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居住了一年,那年夏天的愛丁堡國際藝術節期間,我在讀書會上遇見了幾個英國作家和詩人。其中一個告訴我,他正在幫助他的一個朋友翻譯你的詩歌。
楊: 男得還是女的?叫什麽名字?
川: 男的。是個詩人,叫WH Herbert,他用英語和蘇格蘭方言寫詩歌。那次還有一個美國來的中國女作家。
楊: 叫什麽名字?是用中文寫作還是用英文寫作?是中國大陸來的?
川: 用英文寫作。名字我想不起來了。好象她的作品裏還反映同性戀問題。
楊: 敏安琪?
川: 對,是她。可是我沒有碰上她。她頭天走,我第二天到。 虹影也在英國。
楊: 虹影也住在倫敦。
川: 虹影我的老鄉,但是至今沒見過面。上半年和她通過兩次電話。她和我的朋友傅天琳還有小柏樺他們很熟。 唉!我們還是來談一談詩歌吧!我想,我們先來談一談作家,例如,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一批,就是比如說虹影啦,還有美國的嚴歌苓啦之前的那一批。從詩歌的角度,就是在你的“尋根詩”之後,“尋根小說”那一批,我想聽聽你的看法。事隔十來年了,你又是從國外的眼光來看當年的事情,從時間和空間都有一個間離和沈澱,從文化、文學的比較,我覺得都是很有意思的。
楊:中國是有文學內涵的,從現實題材的厚度也好,複雜性也好,深度也好,絕對應該産生大作品。但是,很多作家本身缺少深度,缺少那種必要的眼光和意識。擺著風景看不見,八十年代有歷史的一定深度,文化的感知,包括對語言的一系列思考,但麻煩的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走得太快太匆促,一下子涉及了太多的題目,但都沒有到達足夠的、充分的程度!然後呢,就是九十年代以後,嘩的一下子轉向了商業。所以,那時的一些作品在文學本身還相當的薄弱,寫作本身的意識還很薄弱,基本上仗著現實本身的豐富性。關鍵在文學本身的思考上。回顧過去,我覺得,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失敗,在現實提問面前的文學的失敗,作品的結構的意識、時間的意識、存在的意識,以及整個反饋出的語言的意識 。
川:你指的語言的意識就是我們討論過的文學本身的創造性?例如說,你提到的尤利西斯?
楊:可以這樣說吧。對現實深度的感覺和語言的創造性是兩個尺度。西方現、當代文學,語言,英語也好,西班牙語也好,希臘語也好,對現實思考的深度和語言的創造性方面都不缺。我認爲,沒有什麽“共同的”現實,一個作家的“現實”只是他揭示在作品中的東西。我們的作家卻是僅就社會現象說事而已……中國文學,如果僅僅是滿足于對現實的表面描寫上,我覺得,不一定能夠寫得出什麽東西來。說白了,到現在爲止,中國文學真正發掘出多少東西?就是說,以前的人沒有說過的東西?我到現在也還存疑。我想象中的成功作品,要麽就是非常徹底的!要麽就什麽都不是,這東西很要勁!
川:去年哈金來的時候,我們就坐在那邊那幾張沙發上聊。北島比他早一個禮拜來。
楊:哦……
川:哈金的小說詩歌都不錯,文論也不錯,人更好,謙和樸實極了。他走了之後,我的幾個朋友都非常地稱讚他。
楊:哈金的小說寫得不錯,我也挺喜歡。
川:哈金他們那一批學外語的冒出來好幾個,法國的亞丁、英國的張戎、我們這兒的張翎。留在國內的有些轉到翻譯和西方文論方面去了。北京、西安有幾個,哈金在早在山東大學搞美國文學。
楊:你對哈金還有些瞭解?
川:是啊,他在山東大學念研究生的時候,我和他通過幾封信,主要是談他們美國文學研究所的幾個文論選題。 後來1987年我到烏魯木齊開會,他們學校來了一個女老師,談到了他,才知道他去美國了,一晃十幾年,後來才從網上知道了他的情況。我注意到了你和他的兩篇文章。
楊:什麽文章?
川:哈金的那篇叫“當代漢語詩歌面臨的問題”,他在文章的開篇就提到你的那篇“中文之內”,你在你的文章裏說,“當代的許多漢語詩人都在‘瞎寫’”,你這樣說,打擊面是不是太寬了?
楊:那你得讀完文章再說。
川:哈金這個人,我的腦子裏,總把他來和梁實秋比,兩人都到了美國,都搞英美文學。
(未完待續)
注:本文經過楊煉及川沙審定
(二)群雄逐鹿——诗歌流派漫谈
川:哈金這個人,我的腦子裏,總把他拿來和梁實秋比較,兩人都到過美國,都搞英美文學,而且,兩人都在山東大學待過。這樣的巧合讓人不能不去對他們有些想法。如果拿梁實秋的《雅舍小品》、《秋實雜文》、《看雲集》、《槐園憶夢》等作品和今天哈金的幾部詩集、小說集、長篇小說《等待》、《池塘裏》等比較一番,無論從那方面,都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既然我們今天談到詩歌,就讓我不得不想起一些關於詩歌的事情。最近看到國內詩人藏棣在一篇文章裏談到對於戴望舒詩歌與臺灣詩人余光中截然相反的看法,北京大學孫玉石關於戴望舒詩歌的研究我以前看過,文學各種流派的存在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從“文章千古事”這個意義來說,不能不考慮到讀者的感受,我從來就不相信那些自吹自己關起門來寫作根本不理會讀者感受的人,這也許跟我當過編輯有關,我知道一些人心裏真正想的什麽。回顧白話詩的歷史,從拓荒者胡適、劉半農、沈尹默到“五四”時期的郭沫若、謝冰心、聞一多、徐志摩、李金髮、馮至、戴望舒、朱湘、殷夫,後來的艾青、田間,再後來的郭小川、聞捷、賀敬之、白樺、公劉、李季,最後到你楊煉、顧城、北島、舒婷、雷抒雁,這期間不過七十年的時段。唐詩三百首,唐三百年,“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領、駱賓王;盛唐巨擘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中唐白居易、李賀、韓愈,晚唐李商隱、杜牧、皮日休等等。三百年就剩下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白居易。南北宋三百年,唐宋加起來六百年出了本《千家詩》兩白首,還是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白居易。及至元明清也有明代前後七子時期發展出來的“竟陵派”、“公安派”,清代袁枚、趙翼等人的“性派”,那時的現象很有些象今天國內的這派那派。
楊:今天的“派別”名稱很豐富。
川:是。而且,每一派都有一些自己的說法 。當然,這中間也有一些流派、詩人及作品對當代的漢語詩歌作出了貢獻。然而,不得不提的是,一些流派和言論,卻總是讓人感到很有點二十世紀那種革命運動的味道。 就是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論,再加上尼采的極端自戀的超人形象的誘惑,否定、打倒和剷除一切傳統價值觀念,文學和藝術陷在了純形式主義的泥淖裏,藝術家、作家、詩人的活生生的真實感受 在一些沒有生命的形式的框架中被抽幹了血液和精髓,只留下一些印刷在編年史裏乾癟癟的空殼符號。詩歌審美被詩歌革命而不是革新所取代,標新立異的簡略化的瘋狂代替了踏踏實實的創作。商品大潮和網路的泛濫,讓一些浮淺的網上寫手重復起七十年代行爲藝術家波依斯“人人都是藝術家”的口號,由反復革命反復造反反復消解政治權威傳染到消解藝術。1991年8月,我在倫敦的皮卡德利圓環附近幾條大街上,就親眼看見毛澤東的標準像在大街兩邊的護欄上一字排開幾百幅,全都瓦雷藝術化,變成了一張張中性的把趣味減到了零的廣告畫。電視畫面上還在燃燒著克裏姆甯宮前面紅場上的沖天大火,那種政治革命波及到藝術領域,革命和革新糾纏不清的歷史畫面讓人的印象太深了。法國大革命的某些方面是在政治上的不負責任,法國人在藝術領域的許多先鋒又先鋒的行爲和流派是不是也有問題,任何事情過了份就走向了反面。拿破倫就是個例子,他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但是最後還是敗在了務實的英國人威靈頓的手裏。你們之後是“後朦朧詩人”,是“第三代詩人”、“第四代詩人”、“他們”派詩人,什麽“知識份子寫作”、“民間立場寫作”、“中間代詩人”、“七十後詩歌”等等。但是,到了今天,還是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白居易。爲首的還是李杜,其次才是王維、孟浩然、白居易等人。才是陶淵明、蘇東坡、龔自珍等人。二十世紀的詩人要和李杜比肩,要和王維、孟浩然、白居易這些大詩人比肩,能不能比,比不比得上去,我認爲,那是二十三、四世紀的人去評論的事情。這不是說個人的偏愛。也許,你和我都有自己偏愛著的在這些公認的名詩人以外的另外一些詩人或他們的某些詩篇。但是,讀者還是讀者。白話詩從胡適、劉半農、沈尹默到你楊煉、顧城、北島才多少年?我覺得不是說不可以比,只是說,從真正客觀公正的立場來看,從“文章千古事”這個歷史學的意義上來看,我們現在只能是自己在心裏去比較,公開來或許會有失公允,至少是太冒失!歷史是後人的事。今天的文壇頗有些象政壇了,幾黨之爭,各寫各的歷史,史學家躲在書齋裏笑掉大牙!明史還得清代人來寫,清史還得民國來寫!當世人寫當世人的歷史,就象今的出國留學生畢業後寫自己的Resume。許多的自編自導。今天是太空行走的資訊時代,唐三百年,唐至今一千三百多年的戲,今天可以幾十年演完,《三國演義》幾十的戲,小孩子在電腦上半小時就演完。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詩歌是情感和技巧的産物,初唐的技巧耗散在承轉發揚《詩經》、楚辭和漢魏六朝詩歌上面,盛唐得以闡發,同時在情感上處於旭日東昇之態,我認爲李杜是處在了“天人合一”的好時候。而中唐和晚唐雖然技巧更成熟,但是,從情感的飽滿度而言,當然,是從“集體無意識”的意義去理解,我認爲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我想知道,你作爲朦朧詩的旗手之一,你認爲,朦朧詩是處於一個什麽樣的階段。雖然,我知道,你對文革地下文學、朦朧詩歌、“今天”詩人,你有你的一些看法,甚至,你對整個的白話詩更有你持否定的態度,但是,我們總得就一個模型來討論和邏輯推演,這有些象我們坐在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磁懸浮列車上觀看牛頓力學時代的蒸汽機車一樣,當然這顯然是不太恰當的比方。
楊:我並沒有簡單地否定白話詩。我強調應把政治社會的轟動效應與詩的文學判斷分開。“朦朧詩”在文學上是很幼稚的,那是一個起步。作爲詩人,難得的是自覺地發展自己。
(三)比“日日新”还新,比“后派”还后——杨炼诗歌简论
川:從你1999年和2000年在《今天》上面發表的十來首“十六行詩”來看,我感覺到你的風格已有較大的變化,和八十年代初在國內一些刊物上,特別是在灕江出版社劉碩良他們搞的那些刊物上,還有北京的一些刊物上那種“朦朧”,還有“尋根”的當時看來十分現代的自由體詩歌有了更加異國化或叫“後”化的傾向。當然,我在這裏談到你的那種“後”化,是指兩個方面的意思,第一個“後”的意思是說的當今的“後”派們那個意義上的“後”。就是指的你的前衛性,毫無疑問,今天你我坐在了加拿大的這個第一大都多倫多來討論問題,這本身就是一個十分前衛的位置,已經是夠“陌生化”或者是說夠“日日新”的了吧!你幾天之內橫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比“日日新”都還要新,所以說,第一個“後”的問題,就是你的作品的前衛性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我感興趣的是第二個“後”。我認爲,你的第二個“後”裏面包含了又是兩個東西:其一是“後院”。也就是“故園”或者“祖國”;其二就是“傳統”。合在一起就是古漢語或者文言文。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表達的是英語詩歌的傳統,用“行”來規範一些東西。中國古體詩裏的三言、四言至七言,樂府、古詩、歌行、絕句等等也是規範,是關於格律、音節、音步、詩節等的規範。在我看來,你的第二個“後”實際上是“前”,或者說是“古”。所以,在我的眼裏,你是一個前後兼顧的詩人,你的作品是古今貫通的。那是指時間。空間上,你又是裏外相容、中外合一的。實際上,在八十年代初期,你就是既“朦朧”,又“尋根”的。我的感覺是,你有你真正獨立的詩歌觀念。這就是我對你的詩歌感興趣和喜愛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是怎麽理解我的看法?實際上,聞一多、朱湘、徐志摩爲代表的“新月派”,何其芳爲代表的“現代格律詩”派,還有後來的郭小川,都有這方面的嘗試、探索和堅持。但是,我感覺得你的作品在這方面有著更大更深更加帶有顛覆性的一些文學嘗試。而且,你一以貫之幾乎二十年來都是如此。臺灣詩評家張默說餘光中是個“藝術多妻主義者”,餘光中的“繼承中國古代遺産”是夏志清認爲“在臺灣論詩及散文無人能及餘光中之重要”的最主要理由*,這幾天“9。11”鬧得人人都在說“原教旨主義”這個詞,這倒讓我想起這個詞安在你的身上大概是最合適不過了。昨天我已經寫了幾頁,題目就叫“一個‘原教旨主義’的漢語詩人”,寫完了給你E-Mail過去,不知你意下如何?
楊:你提到的是我的寫作的兩頭。因爲我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兩卷集,題目就叫做《楊煉作品1982-1997》,其中囊括了這15年我自己認爲還值得保存的作品,而詩歌卷《大海停止之處》中第一個作品,就是《半坡》、《敦煌》和《諾爾朗》,總的題目叫《禮魂》。你提到十六行詩呢,是我在97年後的作品,實際上可以算做我的最新的作品啦!你剛才談到的風格上的變化,我覺得對於一個詩人來說是必然的,也必要的。這裏頭不應該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令人驚訝的東西。從《半坡》、《敦煌》這兩組詩來說,我之所以把它收錄爲我詩集的開篇作品,而把1982年以前的作品都摒除在外,也是認爲那兩個作品開始比較成熟了。之前,不管是朦朧詩的喧囂也好,《今天》的社會上影響也好,作爲詩歌寫作,明顯地受到西方翻譯詩和當時比較膚淺的社會情緒的影響,沒有沈澱出自己對人生、對世界、對藝術的看法。 《半坡》、《敦煌》,是我在80年、81年幾次去西北旅行的結果。最初,我至少記錄了幾百個題目覺得可以寫詩,回到北京後,大概又經歷了將近一年的沈積,才最後篩選出《半坡》和《敦煌》這兩個題目。《半坡》是人類生存處境的一種象徵,而《敦煌》是人類精神文化處境的一種象徵,這兩個組詩某種意義上囊括了我當時對人生和文化的思考。它並不是寫歷史、寫過去, 而是把過去拉入現在,把歷史囊括在現實之內。通過語言重合把它們變成一個在寫作之內的層次。所以,這東西我自己覺得還有一定的份量。後來我寫了一篇序言,叫《重活的孤獨》。點出了中國人痛苦的非時間性,國內讀者沒有太看過《禮魂》之後的作品。人們一般談論的《諾日朗》,也是 1983年的作品。所以等於我在中國的存在到1983年爲止。 實際上從1985年起,我又花了五年的功夫,寫了長詩《衣》(讀“Yi”,這是我自造的字,作爲長詩的總題。)。這部作品1989年在國外才完成的。 這部長詩之後,我有兩本短詩集,《無人稱》和《大海停止之處》。都是在國外寫的作品。1994年到1997年, 又是一個長詩,叫《同心圓》。 也就是收在國內出版的那兩卷集中的最後一個作品。寫完大結構的《同心圓》 ,我才開始寫 十六行詩。 我喜歡形式上的對比,更有意思的是,自從1989年以來,這個分爲兩個八行的十六行詩的形式,時不時常來“訪問”我,如《1989》、《流亡之書》、《死詩人的城》等等,都是用這個形式寫的。 所以,構思新作時,我想,乾脆和這個形式來個素面相對。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這組詩寫作的第一動機是關於形式的。 事實上,寫完了三十首,我才突然發現這種 形式實際上跟中國古代的詞有某種關係。 象上下闋。 我一直認爲中文不很適合一種線性的敍述,它是比較有空間性的。而詞用上下闋, 呈現出不同層次的空間遞進,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是 一種層層建構,而不止是線性發展。我的十六行詩呢, 第一它是在國外寫作的,因此,倫敦,成了一個題目; 一隻蘇黎世的天鵝,成了另一個題目。外表上看,和《半坡》、《敦煌》很不一樣了,很明顯有了一種西方的的迹像,但是,就像我以前說過的,所有的詩的題材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寫作方式。或者說,所有不同 的題材其實都納入了同一個題材,也就是詩 作呈現出的對生存的理解。 我這些詩中的情況,完全一樣。比如《倫敦》那首詩開頭的一行,說,“現實,是我性格的一部分”。這是我走到倫敦街上的時候跳進我頭腦的一個句子。1997年,我剛剛搬到倫敦不久, 一個冬天的下午,在灰朦朦的陽光中, 我環顧四周,心裏一片茫然:這是哪兒?我怎麽會突然落到了這兒?這裏跟我有什麽關係呀?……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一個又一個動蕩的現實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麽?一個積累極長的疑問,突然擰成這樣的一個句子“現實,是我性格的一部分”。
川:是的,我剛到蘇格蘭和第一次到巴黎也有這一種恍若隔世的詩意頓生的感覺。
楊:我想,這個句子突出了:現實完全不是外在的,只是內在的,是內在性格的一種證實。或者說,遭遇早已包含在你的性格選擇之內。 這種內在也要求形式上的自覺, 我的《中文之內》一文就強調“中文性”的重要。比如《一隻蘇黎世的天鵝》中,我不停地交叉“他說”、“她說”,男的他和女的她,那種聲音的呼應啊,一直到出現“五指之美美在死死握緊茫然”這樣的句子。在中文節奏的追求上,“五指之美” ,“美在”,“死死”,“握緊茫然”,讓聽覺失於觀念。 那兒先是兩個“Zhi”,“指”和“之”;又是兩個“美”;最後是兩個“死”……,握緊茫然,指,之,美,美,死,死,那種疊韻,你可以說在呼應李清照的“尋尋覓覓,淒淒慘慘戚戚”!,現在我們對語言形式必須講究,它和以前那種比較粗糙的使用語言已經非常不同了。那麽,對詩的閱讀,也應該閱讀到形式之內去才行,而不該只停在形式外,只關注所謂的“內容”。我認爲,真正專業性的對詩歌的講究,是我們寫了這麽多年詩之後,必須非常明確地提出的一個課題。 簡略 地說。我要求我的每一部作品, 都必須跟以前作品有區別,有跨度。最終的目標是,靠一部一部作品之間的反差,以及它的遞進。 我有朝一日可以把所有的作品編號而成“一部”作品。
川:最近,我在多倫多加拿大中國筆會搞的一次詩歌討論會上,和加拿大華人女作家張翎討論了一些關於當代詩歌的問題。她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叫《望月》,另一部叫做《交錯的彼岸》,她的小說句子裏使用了很多的意象詞,顯得一些段落看上去象徵和多義,像是寫過詩的人轉過來寫小說,細部描寫精美至極。她對我提了許多關於當代詩歌的問題。我對我的回答不是太滿意。所以,有幾個問題想和你探討探討,聽聽你的見解。簡而言之,一是關於詩歌裏的概念的問題,就是說,現在的趨勢是,現代派詩歌幾乎要把概念全部從句子裏攆出去了,概念在詩歌裏的位置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位置?二就是詩歌的社會責任感的問題;三就是當代詩歌的出路。詩壇似乎是從我開始寫詩的時候就離我較遠。八十年代,我就說金牌、銀牌、銅牌、鐵牌、木牌,木牌都發給了狀元。在我的眼裏,詩壇上的一些人,就像是吳敬梓那本《儒林外史》裏的一個個傢夥,當然,情緒來了的時候,我又不得不提筆。寫到了酸處,我就會感到自己也變成了吳敬梓筆端的一個酸人!於是撕掉。小學、中學、大學,我最討厭那些班幹部,文革期間,家被抄了之後,當知青的時候,九十年代出國打工的時候,回國做生意的時候,我看見許多的底層的事情,很髒,但很刺激,很有力度和生命力,才知道什麽是真正的乾淨和高雅!流落到了社會底層才知道“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我知道我是個異類。在國內,我是既不喜歡所謂正統的,也不喜歡在野的。要麽是歌功頌德的,要麽就是標新立異冒酸水的。出國後更沒有太多的時間來寫。一是太忙於生計,二是最近主要是泡在小說寫作裏。但是,上面的三個問題,我還是要請教你。先談第一個,就是詩歌裏概念的位置。你楊煉、北島、舒婷寫了那麽多,讓人記住和傳誦的還是那幾句概念突出的句子,這在很多詩人的作品裏都是一樣。“文章千古事”,我想,大部分還是讓人能懂的部分吧!讀都讀不懂的東西,怎麽個“千古”法?當然,我也喜歡蘭波,喜歡波德萊爾,喜歡龐德、艾略特。
楊:我對“千古”沒有興趣,我最喜歡的屈原,也遠不如後來的一些“小家碧玉”流行,要說“概念”,《天問》通篇都是概念!所以,問題仍不是“要不要”?而是“怎麽要”?“何時要”?這個電子遊戲機的時代,空談“讀者”也沒有意義,“正統”、“在野”都屬標簽,一個詩人,還得向自己裏面寫,孤獨有其必然性(或必要性),“傳誦一時”倒可能是厄運。
川:談到了這兒,我想起你前面談到的關於當今中國文學在文學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就是說,當你回顧中國當代文學的時候,你看到的更多的是失敗,是在現實提問面前的文學的失敗,是在作品的結構的意識、時間的意識、存在的意識,以及整個反饋出的語言意識上面的失敗。說到了底,就是說,當代中國文學在文學本身上面的提升還遠遠不夠?
(未完待續)注:本文經過楊煉及川沙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