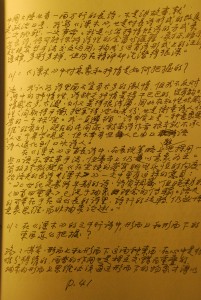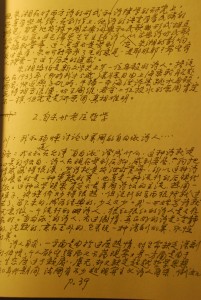洛夫关于此次和川沙《雪楼谈诗》的部分手稿
2002年 雪楼谈诗——洛夫和川沙谈当代诗歌(五)
6 中國大陸的朦朧詩
55川:您對中國的朦朧詩怎麽看?
洛:1984年,我擔任《創世紀》詩刊總編輯時,曾在第64期推出一個“中國大陸朦朧詩特輯”,除了刊出我們一篇評論之外,另有葉維康、壁華、謝冕、徐敬東、孫紹政等的論文,同時也發表了具有代表性的朦朧詩人的作品,如北島、舒婷、顧城、楊煉、江河、梁小斌、王小妮等。1988年以後,我經常去大陸參觀,並訪問各地的詩人,因此除了江河、梁小斌幾位未曾見過面外,其餘都已經相識,尤其在1992年6月我應邀去英國參加倫敦大學舉辦的“中國詩歌研討會”,接著又到荷蘭鹿特丹參加“國際詩歌節”。在這兩個會議中,我都遇見了北島、顧城,不幸的是,顧城在第二年就自殺身亡,其實他在去世以前的數年中,神經就不正常,經常無緣無故號啕大哭,寫的詩意向也很破碎,難以讀懂。而北島身性冷傲,難以交流,我們沒有什麽來往。我是在臺北認識楊煉的,一個高高的漂亮小夥子,詩也寫的很漂亮。在臺北他送了一本詩集《大海停止之處》給我,我很喜歡《面具》這首詩。舒婷也見過幾面,還到她廈門鼓浪嶼的家中做過客。近年來她很少寫詩,專寫散文。
近年來,中國大陸“朦朧詩”的出現,可以說是以70年代末期爲分水嶺的詩變的轉捩點。此處所謂的“變”,實際上就是目前大陸年輕詩人所倡導的“現代化”;這種變,是中國大陸新詩的再生,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不僅限於文學史),因爲它象徵著大陸年輕一代自由心靈的復蘇。但爲何被冠以一個身份不明的“朦朧詩”綽號呢?所謂“朦朧”,其實是大陸一批自覺的青年詩人,在詩觀有了異化的傾向,在對美的認知上有了新的詮釋,且創作出一反以往傳統的新內容、新風貌的詩,但不幸一些党的禦用評論家和素以權威自居的老輩詩人,卻以爲他們逾越了黨的文藝理論與政策而不予承認,便以這個幾乎輕蔑的名詞,作爲對他們向權威和傳統挑戰的一種攻擊口實。對那些權威而言,正因爲已明顯地看出了他們詩中的叛逆性,才會感到刺痛,而老羞成怒。
對中國大陸的詩變,細究其源,我們不難找出幾項促使其變的因素,現分述如下:
第一,觀念性的:大陸年輕詩人幾乎一致認爲,他們詩的變,並不在於語言模式或表現技巧,而主要在於內容。他們要表現的一種全新的內容,那就是對“自我”的追求。在觀念上,大陸詩變的另一項因素是新現實主義的擡頭。此一新現實主義是有別於以往舊的現實主義的框框。吉林大學的年輕詩人徐敬亞,曾在一篇震撼大陸的文壇的文章中指出:“這類青年詩的最大特點是撲面而來的現代氣息——痛切中的平靜,冷峻中的坦然,時代的大喜大悲被他們轉換爲獨白式的沈吟……他們的詩,細節形象鮮明,整體情緒朦朧,內在節奏波動性大,類似意識流的手法,結構奇兀閃跳,類似電影中的蒙太奇,使用一套似乎只屬於他們自己的語言。他們詩中所表現的現實,其實也正是臺灣詩人所謂的“內在顯示”。在表現上,有些詩人傾向于外在的現實的描繪,有些則專注于對內心現實的探索與表達。所謂“內在表現”,就是詩人對生存空間的獨特感受、思考,以及超越現實表層而獲致一種形而上的醒悟。臺灣的前期現代詩人大多側重內在現實的表現,大陸新生代詩人在這方面晚了一大步,但他們實驗的新現實主義,確已使他們的作品有了深度。
第二,藝術性的:大陸文壇反“朦朧詩”的吆喝相當聒噪,但支持者的聲勢也不弱。文藝評論家謝冕和孫紹振就是兩位有力的辯護者。謝冕指出:“我們的新詩,六十年來不是走著越來越廣闊的道路,而是走著越來越狹窄的道路。三十年代有過關於大衆化的討論,四十年代有過關於民族化的討論,五十年代有過關于向新民族學習的討論。三次大討論都不是鼓勵詩歌走向寬闊的世界,而是在左傾思想的支配下,力圖驅趕新詩離開這個世界。”
在這種情況之下,大陸上以新的手法表現新的內容的現代詩乃應運而生,孫紹振稱這一新詩運動爲“一種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於是,以自由表達的方式,追求一種真誠的、人性的、和諧的人生境界與藝術境界,便成爲今天大陸覺醒後的年輕詩人所標榜的新美學。
第三,代溝上的:數十年來,大陸上的詩歌一直是沿著政治主題挂帥的路線發展,詩人都是以直接淺白的語言,寫一些沒有個性、千篇一律的呐喊詩,或歌德詩而起家、而成名。年輕一代對他們不滿,乃另辟蹊徑,自創新調,因而形成兩代之間的尖銳對立,詩中很明顯地表現出“長江後浪推前浪”,新人欲從老人手中接棒的迫切心情。“一代新人換舊人”,這本來是文壇上的正常現象,但由“大老感”、“權威感”和“正統感”所培養、所嬌縱成的大陸詩壇前輩如臧克家、艾青、田間等,卻視新生代詩人的創作爲“離經叛道”,而深惡痛絕,而肆加撻伐,乃構成了大陸詩變的最大障礙。
讀完大陸新生代的詩作和理論之後,我們不禁要問:如僅就詩的本身而論,他們標榜的“現代化”,將來究竟會發展到何種程度?與臺灣的現代詩相比較,二者有何差異?事實上他們的現代化,目前所做到的,只是消極性的反七十年代以前的新詩傳統。由於環境的閉塞,吸引外來影響的困難,他們並未積極地介入世界性的現代文學潮流。
56川:象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哲學理論,我和楊練也談到過這個問題,有一點意念上革命的味道。
洛:不錯,是一種詩的革命,雖沒有流血,卻也使許多人流淚、冒冷汗。新的要否定舊的,舊的當然不高興。不過詩學問題,可以爭辯,不可人身攻擊,鬥爭手段只能用在政治上。朦朧詩人高喊打倒艾青,如果艾青的詩好,是打不倒的。如若他的詩不好,你不喊他也會倒。艾青有艾青的時代,他的詩有那個特殊時空下的特色,至於他的詩能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讓歷史去評說吧。
57川:當然我們要承認他們在那個時代的建樹。就如同不能因爲愛因斯坦的出現就否認牛頓,沒有牛頓就沒有愛因斯坦。當然艾青那一代是有不足,但你不能完全否定。我覺得用革新這個詞好一些。
洛:朦朧詩人反老一輩詩人稱之爲“革命”或“改革”,我是可以理解的,但第三代詩人,本身還沒有成熟,還沒取得詩人的地位,便喊著反北島、舒婷,對這點我頗不以爲然。朦朧詩人是你們的開路先鋒,你們這些人是吃他們的奶水長大的,你們現在的作品不見得比北島、舒婷更好,你們反來反去,又能證明什麽呢?年輕詩人都有“自我膨脹”的通病,臺灣也是如此……
58川: 可以就觀點上的問題進行討論,但不要涉及人身攻擊,比如有些人提到北島,甚至提到了北島的戀愛上,就有點人身攻擊的味道了。詩可以狂妄,詩人不要狂妄。當然,詩人必定是有些偏執的,但是,不要老是讓自己處於那個狀態,特別是面對學術爭論的時候。
洛:P21“狂妄”要有條件,要有本錢,“天子呼來不上船”,李白可以狂,反封建反禮教的竹林七賢也可以狂,但山東有一位詩人,既狂妄又自大,自我膨脹得沒有邊。聽說去年諾貝爾文學獎,可能落在一個中國人的頭上,他便守在收音機旁邊,一夜沒有睡覺,苦苦守候著幸運的降臨,他把諾貝爾獎當作彩券了。
59川: 成都也有這麽一個人,我在1998年就親自遇到這麽一個人,在成都市委大門前紅星路口的一個小餐館裏,他拿手機和別人說話:199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是誰誰誰,2000年的諾貝爾獎一定是我!一定是我!一定是我!2001年逃不過肯定會是誰。正在吃麵條的我只有把碗筷擺了下來,我有些奇怪地擡頭去看他,我們兩人就那麽面面相覷地相互望著,他好象看出我眼裏的複雜的態度,但是,那樣好象是更加激起了他偏要那樣說的願望,他反而越講聲音越大。他講了幾個方面哪些人超不過他。他是很肯定的。他好象已經給瑞典諾貝爾文
學獎評委會把准了脈。這個人如果能看到這篇文章後,我希望他能跟我聯繫,我真的很想認識他。他說的也還很有些道理,北島哪些不行,莫言哪些不行,歐洲的和美洲的哪些哪些作家的哪些哪些東西有哪些哪些不行,爲什麽不行,分析得很認真。我當時就這麽望著他,他也看著我,我當是想去和他說話,但是又有急事,我就走了。我想,他一定是一個人物,樣子還長得英俊,當時我的心裏就很有一種惜才的感覺。很奇怪的,他講的還非常確定。這麽大個中國,只不過窮,怎麽就讓那些獎項都讓西方人拿了?而且有些拿獎的真的並不怎麽樣!中國的很多億萬富翁真的是沒有什麽眼光,說得不好聽是沒有什麽文化,就是人文方面的文化,中國人都知道文章千古事,但是他們骨子裏又最輕賤文人。他們爲什麽不在這千古事上面給予一些捐贈,同時讓自己變得千古呢?諾貝爾肯定是要千古的。我希望中國的有眼光的新型資本家們能夠出幾個諾貝爾式的人物。有些詩是這樣,我和哈金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大陸這些年的詩人比較缺乏古典詩的營養,還有關於朗誦的問題,詩歌的聲音的問題,今天的詩有多少適合朗誦?詩和朗誦是否應該結合?
洛:你最後提到的詩的聲音問題,的確值得重視。早年我寫《石室之死亡》的時候,只注重意向的營造,追求思想的表達,而忽略了詩歌藝術的另一種要素,那就是詩的節奏,所以詩讀來有些“硬”,有點“澀”的感覺。意向和節奏可以說是詩的兩隻翅膀,缺一詩都飛不起來。這個問題我在讀法國蘭波的詩和中國古典詩才悟了出來。我中年以後的詩就特別講究節奏的變化,每寫完一首,總得念一念,拗口的字就得換,改了以後再念,一直改到自己滿意爲止。所謂自己滿意,就是要使整首詩的聲音符合內在的節奏。這種節奏並不是押韻,而是像呼吸一樣自然順暢。押韻是人爲的聲音,一首詩滿篇押韻,讀起來反而不自然,顯得做作。詩貴創造,也貴自然,詩是人做出來的,但必須做的不彆扭。今天中國大陸,仍有一些詩是押韻的,臺灣的詩自從進入全面現代化之後,就再也沒有人押韻了。
60川:加拿大的《環球華報》曾經向我要詩,我拿了幾種風格的詩歌給他們,但是他們選中的讓我有些失望,選的都是他們認爲一般人比較能夠讀得懂的東西。但是,很多讀者喜歡那些詩,也是很好的事情。一些我認爲很好的東西他們完全讀不懂和認爲不可理喻。在我近年的部分詩裏,我把詩裏人的社會屬性抽掉,回歸動物的本性,生物的本性。就象一個畫家從寫實主義走向超級寫實主義,最後在另外一個更高級的層面上倒回去把描寫物件的社會屬性全部濾掉。抽象出更純更高級的東西。我自己感到很過癮。而且很美,很超時空,很永恒,就象遠古的岩畫。我看,藝術的東西很多的是殊途同歸,中國的畫家羅中立近年的畫也是走了這條路。他的畫面上的人的精神狀態被處理得象植物。和他當年得獎的《父親》那幅超級寫實主義風格的畫大相徑庭。可是,他們讀不懂。所以,這也是一個矛盾。我試圖在阿赫瑪托娃、索德格朗、艾略特和惠特曼、特德·庫塞之間,或者說,在你洛夫、楊煉和極端的伊沙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就是說雅俗共存,當然,不是要去遷就讀者,但是,說到了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廣大讀者也有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是他們當中的一份子。既要自己滿意,又要讀者滿意,很難,但是,值得探索和思考。走向民間和走向殿堂,兩條路相反方向,我覺得,還是要看詩人自己的特質,詩的本質不是技術性的,所以,在技術上調整可能還是次要的,主要的還是詩人本身的詩觀念。兩條路,或者很多條路,只要做到了極至,都可以是優秀的,都可以開花結果。花園裏本身就應該是百花共存的,你很難說什麽顔色,什麽品種的花更好看,各有各的好看。
洛:詩人不可以討好讀者,遷就讀者,可以把讀者當作監督家,如果讀者搖頭,你可以反省一下,但不能按照讀者的意思完全改變自己。電視連續劇可以迎合觀衆,甚至依照觀衆的要求修改劇本,但好的電影重視創意和藝術品質,決不會被觀衆牽著鼻子走。但吊詭的是,詩的確需要讀者,詩人應該有一種內心的隱蔽被人分享的快樂,可是你在語言的建構上得爲讀者留下一些通氣孔,一些暗示。我不贊成詩寫的太白、太直接,但你總得給讀者一些線索,就是想象空間。有些詩人對於宇宙人生有著特殊的體悟,這種體悟不是一般日常言語所能表達的,便採用一種曖昧的方式。這種暗示手法通常用來傳達一種哲思或啓示,可以收到不言而喻的效果。佛祖在靈會山上說法,希望從僧徒中物色一位衣缽傳人,他沒有長篇大論說教,只手捧一束花坐在那裏一言不發,下面的衆僧都望著他發呆,這時只有尊者摩珂迦葉,沖著手持鮮花的佛祖微微一笑,佛祖也報以一笑,便把衣缽傳給了他,並鄭重宣佈“吾有正法眼藏,實相無相,付囑摩珂迦葉。”這就是佛教最有名的“拈花一笑”的典故,這種心靈溝通的方法就是詩的暗示方法。我現在隨便舉兩個例子:
在未有眼睛之前就先有了淚 (周夢蝶)
從鋼琴中哀麗地旋出一把黑傘 (瘂弦)
我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梨 / 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洛夫)
這三祖詩分別傳達出一種生命的訊息,一種苦澀的生命情境。這種訊息等情境不是說出來的,而是讀者根據意象提供的暗示體悟出來的。當今所謂“民間”派的詩反對這種暗喻,詩的語言只是大白話,寫的好的只是一篇散文,寫的糟的簡直粗俗不堪。

川沙与北岛
7 北島、楊煉、高行健、夏志清、黃翔、梅娘、戴望舒
61川:對楊練的《大海停止之處》你怎麽看?
洛:楊煉的意向語言有點我早年《石室之死亡》的風格,奇詭也奇險,原創性強,但也艱澀,我喜歡其中的那首《面具》,跟我《漂木》中某些表現手法很近似,我不是說我和他之間有什麽相互影響之處,但同時代的詩人難免會有偶然的暗合。
62川:北島近年的詩好象是越來越艱澀。
洛:提到北島的詩,大家都會立刻想到他《回答》一詩的兩句格言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所有的詩選都會選這首詩,所有的評論家都會引用這兩句,好像這兩句成了北島的商標。正如餘光中的《郵票》,鄭愁予的《錯誤》,其實這三首詩都不是他們最好的詩。詩的讀者一向很懶惰、判斷力很差,只要是流行的詩就是好詩,結果他們的其他好詩反而被讀者忽略了。
北島早期的詩並不晦澀,《回答》這首詩何曾朦朧?不懂詩的人,讀慣了政治宣傳品的人,才會說這種詩是朦朧詩。不過北島出國之後更加西化了,讀來翻譯味很重。有一次在國際詩歌研討會上,他說他開始寫詩受到外國詩翻譯的影響,而對中國古典詩則不屑一顧,事實上大陸新一代的詩人都是如此。
63川:他和高行建的路走岔了,高行建是吸收了法國的東西後,還是寫中國的。我的一個畫家朋友王以石,在法國賣得很好。他畫油畫,把中國古典的東西,蔣門神呀,武大朗和潘金蓮呀和背景的法國香榭麗大道,賽納湖,混在一起,看似光怪陸離,實際上有強烈的中西文化對比的趣味。我說他是70%的中國的東西,30%西方的東西。感覺很好,很多人都收藏。高行健的風格也是那樣,我讀他的作品的主要感覺是《尤利西斯》的樹幹上長滿了沈從文的樹葉,最後,長出的是一種他自己的果子。所以我想,北島走的是不是另外的一條什麽路?
就是李歐梵說的,走向詩人自己的內心。但是,在詩的形式上,他好象顯得更加“朦朧”,更加西化,更加非社會化。我想,對北島詩歌更爲定評的話,可能還要經過一些時間。其實,國內的很多詩歌,他們的詩風,很多是和伊沙相反,好象是越加朦朧,越加讓人讀不懂,越加西方化,才是好詩歌,實際上,仔細讀的時候,感覺到那種詩歌內在的混亂、乾澀、故弄玄虛、無病呻吟。個人內心世界的東西還沒有抒發好,卻有太多對外部世界空泛虛浮的東西。個人的風格還沒有形成,就開始立起來什麽門派,黨同伐異開來。
洛:中國新文學作家接受西方的影響是很正常的事,這條路線通常是先走西方,然後在回到中國來。但要使中西兩種文化在作品中融合一體,卻不是件容易的事,中西文化拼湊在一起並不難,但使兩種不同的東西熔在一起而成爲一種新的有機體,則需要極大的創造力和功力。
這一點,高行健做的不錯,我是說他的小說和戲劇,至於畫,我保留我的意見。

川沙与媚娘
64川:高行健在戲劇探索方面很有研究,趙毅衡在他的那本《建立一種現代禪劇——高行健與中國實驗戲劇》裏,對他的戲劇分爲了三類。一類是“探索介入劇”,象《絕對 信號》、《車站》、《野人》和《逃亡》;二類是“神話儀式劇”,象《靈山》、《冥城》、《山海經傳》;第三類是“禪式寫意劇”,如《彼岸》、《對話與反詰》、《夜遊神》和《八月雪》。並提出高行健創立了一種新的戲劇美學,指出了他的現代禪劇在世界戲劇史上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趙毅衡的眼光,因爲,趙毅衡的那本專著是在1999年,也就是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兩年出版的。我試著寫過幾個劇本,所以,我比較注意高行健的戲劇狀況。1988年,我開始看一些劇本,1990年以後,國內先鋒派的劇本我幾乎都看,什麽高行健前面提到的那些劇本,還有孟京輝的東西,牟森根據馬原小說寫的《傾訴》、刁奕男的《風雨保爾·科察金》、黃金罡的《阿Q同志》、黃紀蘇根據達裏奧·福的劇本改編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廖一梅的《戀愛的犀牛》,還有你前面提到的昆明詩人于堅的長詩劇本《零檔案》,于堅對高行健的後現代詩劇《彼岸》寫過一篇文章,名字叫做《關於彼岸的漢語語法討論》。他們很多人是中央戲劇學院的,劇本是在中央實驗話劇院的小劇場演出。也有很多是西方的劇本,象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瑞士的馬克思·弗裏斯(Max·Friseh)的《安道爾》,還有尤內斯庫的成名作《禿頭歌女》、薩廖爾.貝克特的所謂當年在世界劇壇最匪夷所思神秘莫測的劇本《等待戈多》。還有義大利的R·基迪的未來主義戲劇(Futuristic Theatre)《黃與黑》(Yellow and Black)那一類的劇本。孟京輝是個很有創意的人,例如他的一出名叫《思凡》的劇,就是根據中國明朝無名氏的《思凡·雙下山》和義大利的浦伽丘的《十日談》裏的章節改編,講一個叫色空的小尼姑在仙桃庵內度日如年,她不忍寂寞,思念凡間世俗,逃下山的路上與同樣從和尚廟裏逃出來的小和尚本無相遇相戀,後來又鬧出一些法國喜劇式的笑話。
洛:高行健的成就要總體來看,除了小說《靈山》之外,他還有戲劇、評論、繪畫。他的法文究竟好到什麽程度很難說,但他的劇本卻在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上演,且頗受好評。臺灣的戲劇家就很肯定他。去年(2002)他的《六月雪》在臺北上演,即曾獲得臺灣政府大量的經費支援。中國作家比他好的不乏其人,但他的綜合創造力,和把自己的作品寫成外文推向國際,還有誰比他更有這種優勢?
65川:我覺得他的作品總的一個姿勢是逃的姿勢,美國的約翰.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裏的兔子是從險惡的社會網向外逃,向女人的懷抱向性愛裏逃,美國文學稱他的作品是“美國中產階級風尚的經典史詩性作品”。高行健是從無所不在政治空氣裏向藝術領域裏逃,因此,他的作品看上去顯得對人間社會、尤其是我們所熟悉的政治社會,那裏面的人和事很冷。這顯然是他的前半生在中國政治運動中留下的後遺症。
洛:詩人黃翔對他也有同樣的看法,說他“是個精神冷漠的人,作品表達的只有欲,沒有一絲一毫的情……他對世界也很冷漠,不僅不愛人,也不愛這個世界,對別人的苦難漠不關心,拒絕責任、良知和道義擔當……”我覺得這樣的指責也許有些苛刻,真正對這個世界冷漠的人,就不會寫這個世界了。他可能在海外只搞他的文學藝術,而不熱心于民主運動,不介入政治,我以爲人各有志,不做民運人士不見得就沒有良知和道義擔當。我們不能完全把高行健定位在“流亡作者”上,他有這方面的糾葛,但不完全是,他跟前蘇聯作家索忍尼辛不一樣,索忍尼辛是爲了反蘇聯共産極權而寫,高行健不論在思想和題材上都超越了他。
66川:您談到:詩歌象宗教一樣,越落後的地方,詩歌越發達,這一點臺灣大陸都一樣。您爲什麽這麽看?
洛:今天不論在中國大陸,或在臺灣,詩的生長環境都十分不利。如果純粹從市場經濟和現實的因素來看,詩的邊緣化,詩的産銷情況,的確令人失望。不過有一點我們不能忽略,這就是詩的價值從來沒有人懷疑過。詩集賣不掉並不代表詩人創作熱情的消退,貨賣識家,詩贈知音,有人諷刺詩人說,詩人比讀者還多,我認爲這也正常,詩的讀者肯定比瓊瑤的讀者少,而大衆化的詩人,詩的素質肯定上不去。我甚至曾說過:“我的詩是寫給詩人看的。”
我寫詩50多年了,是一個近乎癡狂的詩的追求者。經常有人問我:是一種什麽力量使你如此堅持而不放棄?我的回答是這樣:年輕時寫詩只是爲了興趣,沒有什麽高的追求,後來與朋友辦了一個《創世紀》詩刊,才全心投入,把寫詩當作終身的事業來經營。其實寫詩完全是一種沒有現實利益可圖,一種非常個人的,也十分孤寂的工作,但能堅持數十年而不懈,內心必然有某種動力與信念在支撐著,這個動力與信念就是:一開始我就不以爲市場價格觀念來衡量詩歌,最初領稿費時還覺得不習慣。第一次拿到台幣數十萬的獎金時,就好像發了意外之財。我永遠是以“價值取向”來規劃我的創作生涯(我相信絕大部分詩人都是如此)。我認爲寫詩不只是一種寫作行爲,而更是一種價值的創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創造,生命內涵的創造,和意象語言的創造。總體而言,就是對一種絕對之美的創造。
此外,就文化的發展軌迹來看,我對詩歌的前景還是看好的。我認爲詩歌和宗教一樣,在兩種極端的情況下會得到高度的發展,一種貧窮落後,一種是繁榮富足,比如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詩歌相當興盛,一場詩歌朗誦會,可以吸引數千位的聽衆。在臺灣也是如此,因爲那時大家都窮,物質上的匱乏只好在精神上得到補償。而今天,中國的經濟正在起飛,生活條件初步轉好,先求得物質的滿足再說,詩歌這種不及之需不妨暫時擱在一旁。但我相信,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文化的繁榮,當經濟與社會發展到某種高度,物質已能得到滿足之後,人們又會回過頭來追求精神的調劑,於是詩歌等其他的精致文化,如繪畫、音樂等都會成爲豐富這個新時代的精神內涵。我國的盛唐時代,和20世紀的歐美社會就是最好的證明。這雖是我個人的樂觀想法,但我相信這種樂觀前景是可以期待的。
67川:你提到,徐志摩,是否可以打一個比方,他主觀上不是要迎合什麽東西,但《朗橋遺夢》、《失樂園》是針對一群物件寫的,但徐志摩不是要針對什麽,可能他主觀上就是這樣。因爲,在他的那個年代,並不象今天這個時代的作家和導演們那樣對於藝術品的市場定位和分析那麽精細、算計和刻意追求。例如美國好萊塢電影的製作過程中斤斤計較的步驟。
洛:徐志摩是一個尚未完成的詩人,可惜英年早逝,詩的成就有限,如果他活的久一點,很難說他會變成什麽樣子。以他現有的詩來看,數量與質量都不能成一個大詩人。他已被定位爲抒情詩人,其實抒情詩人也有等級的,他名氣大,詩藝卻不相符。他的名聲多半來自他那些富於社會轟動效應的戀愛和突然的死亡,至於詩,我認爲是青年詩人不可學的反面教材。我並不否認他是一個純真的詩人,熱情的詩如不通過語言的提煉,最後表現的仍只是熱情,仍只是膩人的調子加上那種夢幻的浪漫情緒,讀多了會倒胃口。徐志摩的確不是爲了迎合什麽人而寫詩,他是天生的風流(浪漫),但缺乏詩的觀念,也沒有詩的語言,更缺少對深層生命的體悟,所以他的詩一覽無餘,毫無縱度。嚴格說來,他是低俗讀者心目中的詩人,而不是真正意義下的詩人。
68川:你是否認爲抒情詩的段位比較低?
洛:那倒不是,世上的詩除了史詩性的敍事詩、詩劇,其餘本質上都算是抒情詩,中國的文學傳統就是抒情詩;但抒情詩確有等級,李白也算是一位浪漫派的抒情詩人,但徐志摩的段數簡直就沒法比。
69川:《朗橋遺夢》出版後,香港的一個女評論家說:《朗橋遺夢,遺了什麽?遺了一灘精!》,還有日本的《失樂園》。還有瓊瑤,是否就是一種煽情?
洛:《朗橋遺夢》我沒有讀過,故事想必好看。如果這位作者是一位後現代主義者,可能真會把書名改爲《朗橋遺精》。日本的《失樂園》,我看過電影,但不認爲煽情,而且是現代化的《金瓶梅》,許多做愛的鏡頭。描寫情欲的電影,美國好萊塢拍的最好,譬如《致命的吸引力》,完全是從商業著眼,迎合大衆的口味。
70川:既然我們今天是漫談式的,我不妨還提兩件事。一件事就是這次來之前,從我們的幾次電話和我收集和研究的一些資料裏,我準備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大概就叫做“1953-1980當代中國斷代詩學史上的脊梁–洛夫”,爲了不失公允和偏頗,裏面當然會談到藍星詩社,當然主要就是余光中和他的作品了,他畢竟領軍的人物。但是,既然夏志清等人對他已有一些定評,我就不想再去過多地探討他。但是,問題出在夏志清的定評上,我在中國大陸的時候,很多次會上聽人們談到,他老人家的話就象一根掄起來打人的棍子,好象他在美國說的話就是什麽金科玉律似的。我覺得,在我們中國人的傳統裏面,都有一種霸氣、匪氣和山大王氣,西方人,義大利西西里島上的人稱之爲教父,中國人稱之爲舵爺,可是在我們中國人裏,連學術領域也概莫能免。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夏志清的“定評”是不是太多了和太早了。定評一般是做在被定評的人去世之後,就是我去年和楊煉談話時我堅持的看法。當世人的事情最好不要當世人去下什麽結論,而且,切記不要去下那種對別人終身學術成就的定評。老師給一個學生的一篇考試卷子可以下定評,他學期完了,你可以給他些個評語,對一個作家的一部作品,可以由評獎委員會的評委們去說三道四。但是,不要動不動就去給人家一輩子下個什麽結論,那是很危險的。特別在一個地區去說某某某是什麽第一的話。夏志清在論及余光中時就說過“在臺灣論及詩與散文無人能及餘光中之重要。”[4]我並不是說餘光中的東西不好,我也很喜歡他的散文和部分詩歌,而且,我認爲非常地好。但是,我覺得,夏志清先生的話太過武斷和缺乏說服利,而且危險。撇開你洛夫先生,如果在若干年後,我們後來的人發現原來臺灣和餘光中同時代的某某某原來他(或她)的作品是沒有被當世人引起重視的一部劃時代的大作品時怎麽辦?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文學作品,藝術作品,往往越是大作品,越是在滯後體現,我想這方面你知道更多的例子。我知道的例如尼采、焚高、還有寫《大白鯨》的麥爾維爾等等。我們都知道,夏志清對張愛玲的“定評”後來是改了口的,他自己也知道結論下早了和說得有失偏頗。前年,我和梅娘(孫嘉瑞)見面時,從她送給我的書裏看到她在“牛篷”裏關了近二十多年後,中外文學史家對她的評論。梅娘和張愛玲在四十年代曾經並駕齊驅,在中國大陸有“南玲北梅”之說,梅娘當時主要是在北京,她的作品早期是在日本,後來在淪陷時期的東北,那些東西不是張愛玲可以寫得出來的。其中,美國的王德威、中國的張泉、張中行、日本的釜屋修、騰井省三等人都有非常客觀而又肯定的高度評價。[5]作爲文學史家的夏志清卻是在評論中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因爲,他也是後來才看見梅娘的東西。由此,我們是不是可以說一句話,就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要是哪天突然在張愛玲之外又冒出個什麽李愛玲、王愛玲馬愛玲的劃時代的大作品來,下定評的人可不是要更加尷尬了嗎。中國太大,人才輩出,高手如林,埋在土裏,埋在“地下”的東西很多,這對於愛下定評的人來說,無疑到處都是定時炸彈。還有餘光中和中國青年詩人藏棣關於戴望舒的爭論,餘光中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也太過武斷,你不能把戴望舒那樣地否定。關於這些問題,我還得向您老請教。美國的詩人黃翔先生在一九九九年到臺北一次詩歌獎領獎後,對於文學作品及作家的的名譽的看法我看了後,認爲他說得相當的客觀。他的話是:
“一個詩人是否真是詩人,他一生的創作成就也不是由哪次獎來作出評估的;更不是由哪幾位評審委員來作出判定的。任何一種獎只具有相對的參照意義,它只是對一個詩人的創作、哪怕是一首詩的評價標準之一。一般的獎如此,諾貝爾文學獎也如此。因爲人類精神世界氣象萬千、豐富多元各有各的取向、各有各的好惡、各有各的趣味。詩學見解和美學標準千差萬別。詩歌只有不同層次上的區別,所以可以見出大詩人或小詩人、或者詩人和寫詩的人;但同一層次上卻只有個性風格彼此迥然相異卻絕無高下之分。而詩學中真正的大家在一個時代卻極爲罕見,屬少數;因爲這樣的人必須兼具各種因素和各種才能的綜合。而大家往往反而很難得到世俗社會的認同,也許得獎的機遇可能相比之下更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得獎的未必是最好的詩,未得獎的未必次於得獎的詩,也很可能更好。如就諾貝爾文學獎而言,托爾斯泰就未得獎,儘管他的文學成就遠遠超過許多獲獎者。”
我覺得,黃翔先生說得非常到位。一些達到了相當水平上的作品和作家,你很難去說誰的東西比誰的東西更好,因爲,那種可比的因素在哪里呢?數學上的函數關係裏面還可以列出幾個XYZ的變數,文學作品,一個作家,一個詩人一生的成就,你怎樣去拿來和另外的作家和作品比較呢?文學和藝術不象體育競技,每秒的速度,舉重的重量,拳擊臺上誰把誰打倒在地沒有,球踢進去了沒有?文學作品的好壞,作家的水平,我的看法是一個公衆認可的問題,認可時間長短的問題。現在有些現象是很奇怪的,作品比數量,結果是作品的數量和讀者對作品遺忘的速度成正比,甚至人們打開書根本就讀不下去。
洛:夏志清這位先生據說英文很好,評論文章不怎麽樣,他的中文文章寫的很囉嗦,批評的態度很霸氣。有一次臺灣聯合報請他回來擔任文學獎的評委,當時他評小說我評詩。有一篇小說爭議性很大,他給的分數很高,其他評委給的分數則比較低,故在決選會上落選,夏志清氣得拍桌子,大聲咆哮:“你們不聽我的,請我回來幹什麽?”據說大家商量之後,做了對他妥協的決定,獎還是給了他堅持的那篇小說,作者是一位元漂亮的女記者。
夏志清的評論不但有問題,言行也極怪異,簡直不可思議。他第一次見到我,便說:“你這位現代李賀也來了。”這次是我和他,還有小說家無名氏,名導演胡會詮,應《聯合文學》雜誌社之邀,搭火車去花蓮給“巡迴文藝營”的學生講課。火車剛開出臺北站,車廂內喇叭聲音太大,很吵人,影響大家談話。夏志清要求服務員關掉喇叭,而這時服務員正忙著,沒有立即照辦,五分鐘後,喇叭聲音還是很大,夏志清氣急了,突然“碰”的一聲,向那位服務小姐當衆跪下了,大家對他的驚人之舉嚇愣了,不知所措,最後還是我親手把他扶了起來。另一次事件也叫人難以忍受,有一次一位文壇大老請他吃飯,記得我與夏志清之外,還有幾位文藝界人士同席,夏志清突然對坐在他對面的一位小說家說:“報紙上說你老兄不是死了嗎?”那位先生聽了臉色大變,冷冷地否認。原來夏志清張冠李戴,弄錯了物件。
他評小說功力如何,我不敢妄斷,但我肯定他不懂詩。他對現世的作家做蓋棺定論,只表示他的輕率,反正也沒有什麽人信他的話。
至於黃翔在臺北領獎時的一番談話,的確說得很有見地。那次他去臺北之前曾打電話給我,要我爲他介紹幾位元臺北詩人認識。他是湖南老鄉,是少數幾位流亡美國的傑出的中國詩人之一。關於“諾貝爾文學獎”我也聽過許多意見。有一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先生應邀去臺北主持一個座談會,我也被邀去參加,當時討論最熱烈時,有位先生提問:“請問馬悅然先生,得諾貝爾文學獎有沒有什麽秘訣?”大家聽了一愣,馬教授也不知如何回答。我忍不住站起來發言說:“文學創作純粹是個人的事,得不得獎並不重要。得獎是錦上添花,作品完成之後,它的價值早已確定,而諾貝爾文學獎是對一個作者終身成就的追認,它不是一般的徵文比賽,哪有什麽獲獎秘訣?唯一的秘訣就是把作品寫好,好到夠這個大獎的條件,而其中另一項很難得條件就是機運。”我一說完,會議中響起一片掌聲。
71川:戴望舒的東西寫得很好,是那個時代的代表作,是新詩發展過程中,以最少的數量領導一個流派的詩人,到今天來說,他的東西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我在念大學的時候,眼裏的幾個學校裏的詩歌尖子都看他的東西。我的一個朋友,一個數學系的詩歌愛好者就十分珍惜地藏著他的詩集。朱自清、施蟄存當年對他有很高的評價。三十年代在上海和戴望舒並駕齊驅的還有寫小說的施蟄存、穆時英、劉呐歐,他們被李歐梵稱爲新感覺派,並認爲他們三人是中國現代小說的先驅。我的感覺是,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確實是中國“五·四”以後,整個東南亞地區文學作品和人才異彩紛呈的地方。因爲,當時的上海是一個國際大城市,是一個比東京、新加坡都大很多的城市,不單是地域,更主要的是指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是整個東南亞的中心。有些象倫敦和巴黎在歐洲的地位。所以,餘光中在北京大學的發言明顯地欠妥。
洛:餘光中在北大演講中批評戴望舒,藏棣提出反駁,這件事我也聽說過,我認爲雙方爲文學問題爭辯,都沒有錯。在中國大陸,戴望舒是新詩界的高峰之一,讀者心中的偶像。但偶像並不是不可以批評的,以今天的文學讀者來看,五四以後和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也確有不成熟之處 ,但以現在的眼光來評價當時的作品是不太公平的。余光中在文章中挑朱自清的毛病,我認爲不但有欠公平,而且沒有必要,因爲這是犯衆怒的事。
72川:他的有些詩歌像是散文,有些散淡而缺乏張力。
洛:葉魏蓮是評論家,詩也不錯。但不得志,被壓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