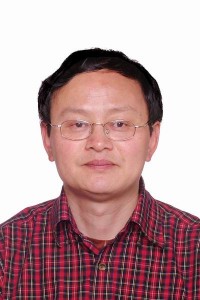黑暗的记忆与光明的期待
——川沙长篇小说《阳光》中的自审式沉思及其意义
原载美国《中外论坛》(East West Forum)双月刊杂志 2005年第6期及2006年第1期
李咏吟 2005年 夏
(2012-11-22 09:1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李咏吟 阅读 13649次
http://www.zgnfys.com/a/nfpl-37988.shtml)
作者简介:李咏吟,哲学博士(杭州大学,1998),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浙江大学古典学与早期基督教研究所所长。学术领域为“诗学与解释学”,著有《生命的智慧:张承志的话语世界》(沈阳,1999),《走向比较美学》(合肥,2000),《诗学解释学》(上海,2003),《创作解释学》(桂林,2004),《解释与真理》(上海,2004),《生生之德:审美与道德的本源》(上海,2006,将出)。在《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九十余篇,目前主要致力于浪漫派诗歌与诗学思想的研究。
一、苦难记忆与诗情表达的意义
《阳光》无疑是一部值得思考的重要作品,事实上,它本身包含的复杂性经验与思想,不仅能激发人们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乃至百年中国历史苦难的重新反省,而且也拷问着我们对民族苦难的责任承担。从各种方式追问民族苦难的根源,正视民族苦难的真实境遇,探究民族苦难的超越之途,在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我试图以这样的“基本预设”来理解作家的意图。自然,关于作家意图的接近,我们可以通过作家的“清醒口述”(沙龙谈话)和“创作自述”(小说后记)获得理解。创作永远是“作家的个人性诗情表达”,作为解释者,我对作家意图的接近,一方面可以倾听作者口述或自述,另方面则必须依托自己的“亲历性阅读”,因为作者的意图更真实地潜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理解了作者的意图,就能清醒地把握作者的长篇小说所构造的心灵历史世界及其意义。从文体意义上说,长篇小说以其恢弘的气度与篇幅,最能自由重构作家的“生活想象世界”,对于严肃的作家来说,长篇小说的创作,意味着他/她的生命历史与意志的话语确证。
正是基于严肃的态度,我反复体察川沙在《阳光》(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中所构造的心灵历史,企图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进行合法性解释。 进入作品,就会发现,作家的具体意图是明显的,他试图通过对“秦田”个人命运与心理历史的把握,重新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后果及悲剧性根源,当然,他不只是为了正视这一问题,还想借此反省百年中国的思想文化迷途或如何走出迷途,寻找中国人生命选择的精神可能性与现实可能性,以及二者之间可能产生的巨大矛盾。据作者自述,在他原拟的三部曲中,给予这一作品的命名是《原罪》,显然,这个题目比《阳光》更显基督教意味,不过,从写作的“文本事实”而言,《阳光》这一命名自然更具敞开性。作者直面的是“原罪”,但在内心深处却渴望着“阳光”,在我看来,这一意图富有特别的创作价值。这促发我们思考:如何探究文化大革命的个体性悲剧与民族性悲剧?从理论上说,对“文化大革命”寻求普遍意义上的深刻理解虽然是可能的,但毕竟显得抽象。
对于作家来说,他首先不会考虑普遍性问题,他永远只能“从个人出发”或“从历史具体性出发”,也就是说,他只能通过个体性悲剧来探究民族性悲剧。也许他可以从“个人性”上升到“普遍性”,但关注个人性才是他的根本目的。因为文学不是哲学,它不要进行普遍性说明或证明,而是要基于个体的历史命运,唤醒人们对历史生命情感的记忆或对生命存在的想象,通过历史与存在的生命想象与体验来完成心灵的认知和觉悟。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的人来说,无数的“个人性体验”,积淀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记忆,在口头叙述和书面叙述中,人们已经将这段历史从不同层面敞开,显然,它大多是“个体性的亲历记忆”,肯定无法获得普遍性认同。必须理解,即使是面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个人记忆,个人经验往往也是完全相异的,甚至是敌对的,虽然也有其共通性。独异的个人经验与反省性价值判断,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某一阶层受难者的精神体验与生存记忆。 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对于亲历者和非亲历者来说,对于受难者和旁观者来说,对于幸存者和苟活者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者不可能进入所有人的心灵世界,只能对同情者与渴望理解者敞开。
我们可以凭自己的记忆去认知中国文化大革命乃至百年苦难历史,但必须充分尊重每一个他者的亲历性,只要他具备基于个人体验与记忆的真实原则。应该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疯狂的历史事件,是一非理性的民族文化事件,是一场惨绝人寰的人民间的血腥仇杀,是中国文化内部等级制度与阶级仇视、极权私欲意志与惟我独尊的生命仇恨的间歇性爆发。对于权力者来说,它只是为了权力和帝王般的疯狂乃至非理性的私欲意志的极端随意实施;对于平民来说,它只是为了反叛等级欺视和发泄仇恨。在我们的大国文化中,生存的艰难与专制的统治使得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仿佛更多嫉妒与仇视。许多人只希望自己高高在上而他人皆为奴隶,中国的帝王思想融入到了许多人的血液中,帝王意志的无法无天与随意杀戮,使民族的“官魂”与“匪魂”合为一体。一个国家的受难和公民的疯狂,构成了虚假意义上的“狂欢节日”。正是少数人的非法的节日般的“魔鬼快意”导致了正常公民的苦难。在历史的顷刻,尊严消失,理性让位,人权失效,只有暴力与疯狂,残暴与体罚,打砸与污蔑,革命者与造反者在非法的时代获得了“特权”,可以随意打击合法公民的“权利”,随意凌辱曾经比自己生活得快乐的人。 在历史反省与理性评判的今天,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否定“文化大革命”应该是理性的选择,不管它当初的思想动机是如何纯正。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公民带来的苦难的是多重的:对于知识者而言,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苦难,它对知识者人格尊严的虐待,是反人类的恐怖精神行为。对于工人农民而言,它剥夺了人正常的生活权利,剥夺了人追求幸福的自由意志,让人承受了饥饿与暴乱的恐惧。也许只有“流氓无产者”至今难以忘怀那野性的非法的任意的虐待他人带来的满足和狂欢。事实上,这些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的人并无悔意,他们今天在年轻人面前依然愿意炫耀“文化大革命”的“狂欢体验”,年轻的倾听者似乎也没有愤怒,甚至充满了羡慕与崇敬。我们不能期待别的角色来反省这一段历史乃至百年或千年中国史,只有知识者才可能重新反思这场洗劫与苦难,虽然不少知识者也在这次革命中扮演着帮凶的角色。受难者和关注受难者,必须反省苦难自身,不能让苦难变成了历史游戏。 川沙以其作家自身所特有的正义感重新反省这一历史,他的创作意义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的视角显然是知识者视角,而且是作为青年的苦难承受者和见证者的视角,这一视角的真实性,一方面使他保持着与真正的受难者的距离,另方面则使他能够反思苦难的根源并寻找未来中国道路的勇气。
在《阳光》中,他赋予一个名叫“秦田”的人来直面和反省这一历史。从“作者的本文”来看,他似乎更多地陷入历史苦难记忆的重构之中,他的主人公直面历史苦难,一时还走不出历史苦难,甚至,在历史苦难面前倍感迷茫。主人公的境遇是:背负历史的苦难重负,惟有让良知平复伤痕。当恐惧记忆永难消失、苦难伤痕永难抹平时,他的精神意志趋向于选择同样的暴力方式来报复,即通过强力专制的手段来反击仇敌。 川沙的《阳光》所具有的多重价值,根源于他通过文学叙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形象化反省。这种“形象化反省”充满着独特的个人性视角和经验。例如,(一)他的整部小说以留英学生之间的感情为情节线索,这使得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反省在异国他乡的现实空间展开。与其说,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撕咬着“秦田”的灵魂,不如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苦难始终压迫着川沙的心灵。他借主人公之口,反复地问:“这是为什么?”“这是谁之罪?”这些朴素的良知提问显示出一个作家的庄严与正义;(二)浓郁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使人们对拯救苦难充满着遐想。川沙在《阳光》置入了大量的基督教内容的叙述。对基督教的信仰,使得“伍芬”这位来自台湾的文学博士生,充满温情与挚爱。但是,期待自己的恋人秦田也信仰基督,并淡忘苦难的伍芬,始终无法理解“秦田”的夜夜恶梦;秦田生活在基督教与自由的法律世界,却无法理解和亲近以法治为依托的文明,无法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恶梦记忆,始终陷于黑暗记忆以及对苦难承受者的感伤与无限缅怀之中。这就形成了文化、思想乃至价值取向的根本对比。(三)川沙在小说创作中有其浪漫主义的想象,故而设想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伍芬的纯朴善良与来自大陆的物理学留学生秦田的精神恐惧之间形成对比,按照通常的理解,人性中美丽的东西总能穿透黑暗,救治伤痛,但是,川沙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伤痛与真正的恐惧,又不是简单的感情治疗所可以抚平的;为此,在美丽与激情,爱情与同情之间,许多复杂的精神体验得到了真实体现。(四)基于对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场景和家庭悲剧生活的苦难记忆,故乡成了川沙叙述记忆中最重要的场景。这个童年的故乡,虽然也曾带给主人公许多美好的“家园记忆”,但是,这个属于家园记忆的地方,却给予主人公以夜夜梦魇,而且永远无法摆脱。
“家园记忆”应该亲切美丽,温馨难忘,为什么我们的家园记忆如此令人恐惧?难道寻求自由与美丽者,只能永远流浪?作者赋予家园记忆以特别的意义,从生存意义上说,显得异常重要,它启人深思。总之,这些“个人性”经验与虚构使得川沙的叙述具备特殊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 文学叙述的“永远的个人性”,一方面带来了创作者与接受者的独特经验,另方面也带来了理解的困难,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苦难记忆,仅仅通过叙述是无法获得普遍性经验传达的。现实的接受情景是:作家的苦难而悲伤的叙述往往变成了异邦读者的好奇或快乐欣赏,因为野蛮自身在艺术中常常具有了观赏性和快感体验,所以,艺术中的战争、屠杀、残暴、血腥有时并不能给人们带来警醒,相反,可能给人带来快意。悲剧如何让人们以严肃的心境来接受和反省是作家的基本追求之一,川沙以其诗情和悲剧叙述获得这种接受效果。
“永远的个人性”虽然不能获得永远的普遍性,但个人的真实具有历史警示意义,只要有某种个人性真实苦难存在,它就不能被我们忽视,这是作家的诗性正义理想。许多人习惯于以社会现状评价的最大公约数来消解他人的苦难经验,这是极不人道的。基于此,可以看到,川沙的《阳光》从总体基调上说,是悲剧性的苦难意识的体验性表达,以及关于个体性生命价值的自审式反思。其中,悲剧性个人经验与幸福性个人经验的错杂,充满了强烈的对比性,读者虽然不能从主人公幸福性的当下个人经验中感受到快乐,但是,面对黑暗的苦难记忆,读者绝对难以无动于衷。悲剧性个人经验具有如此强大的约束力,这就是川沙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