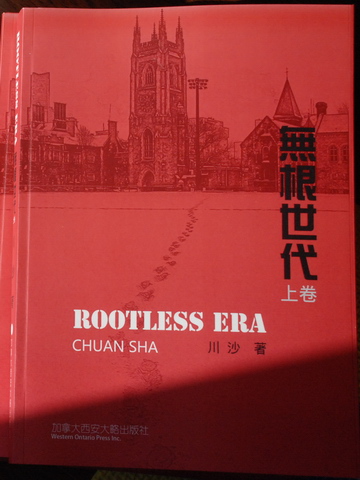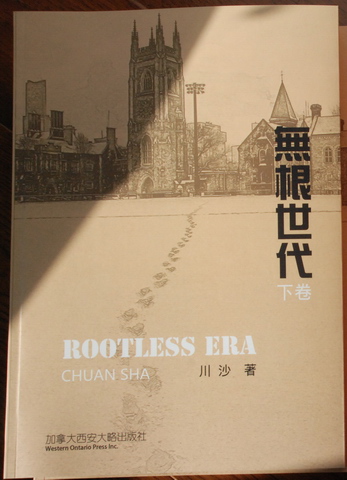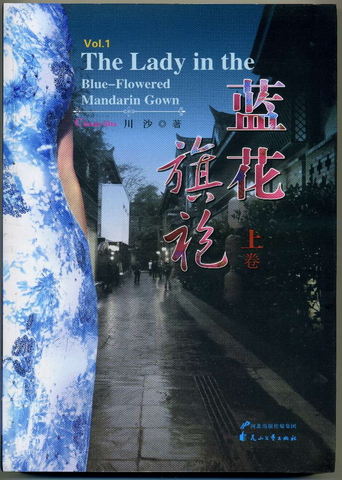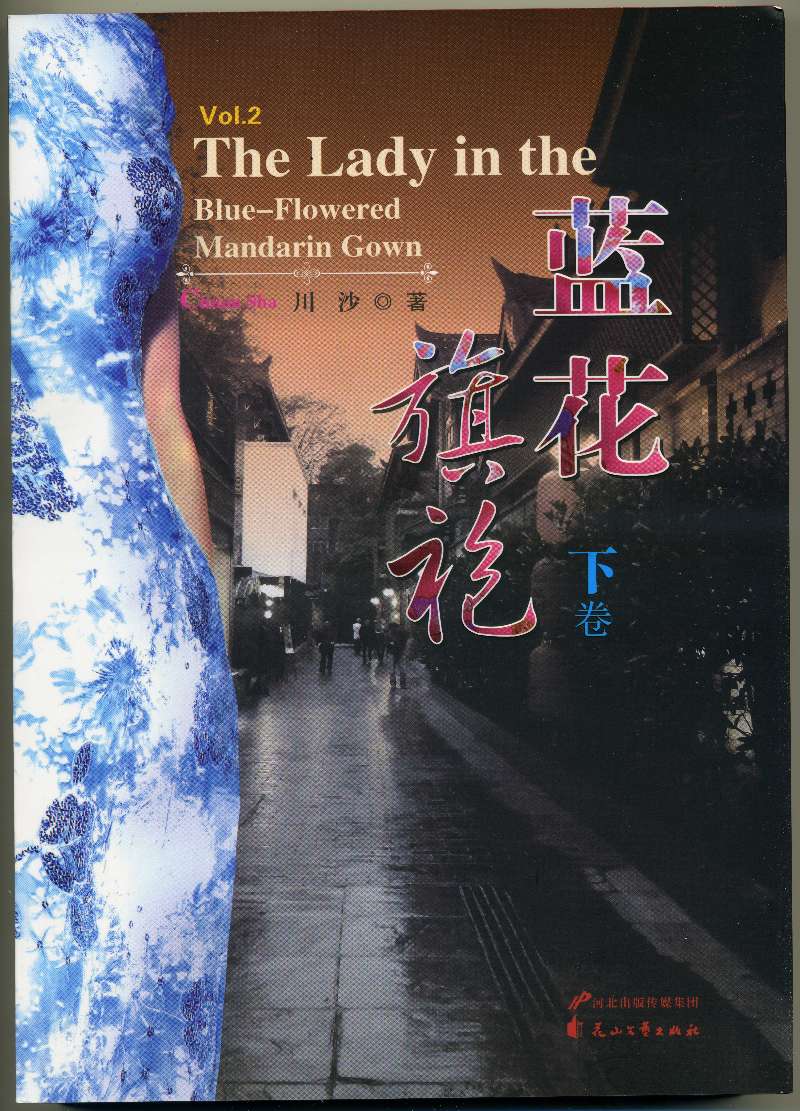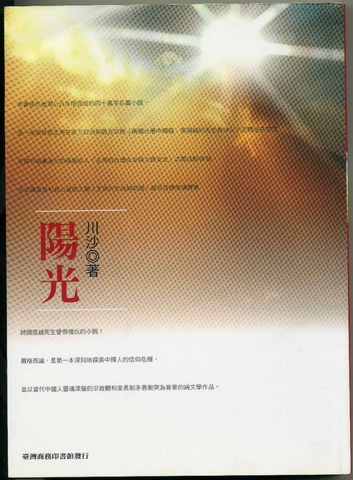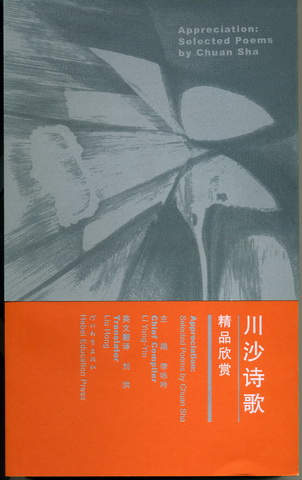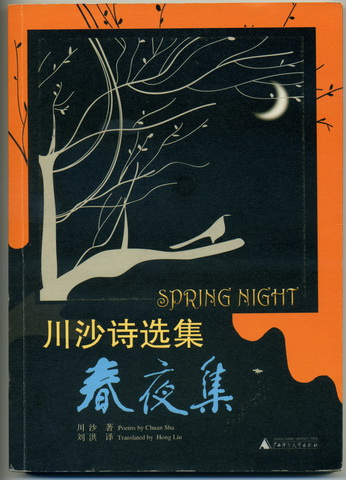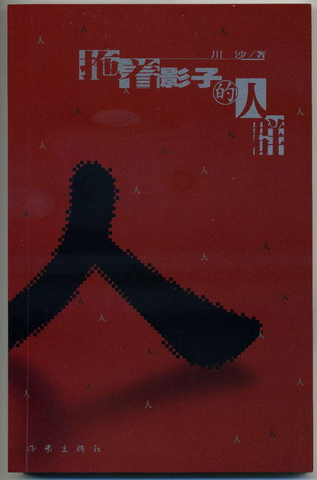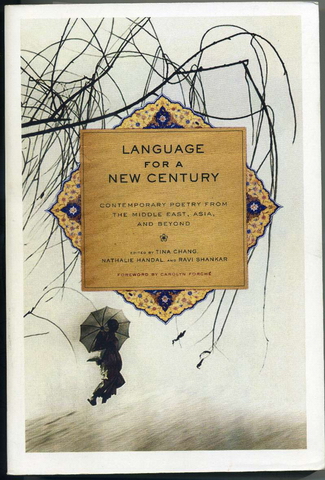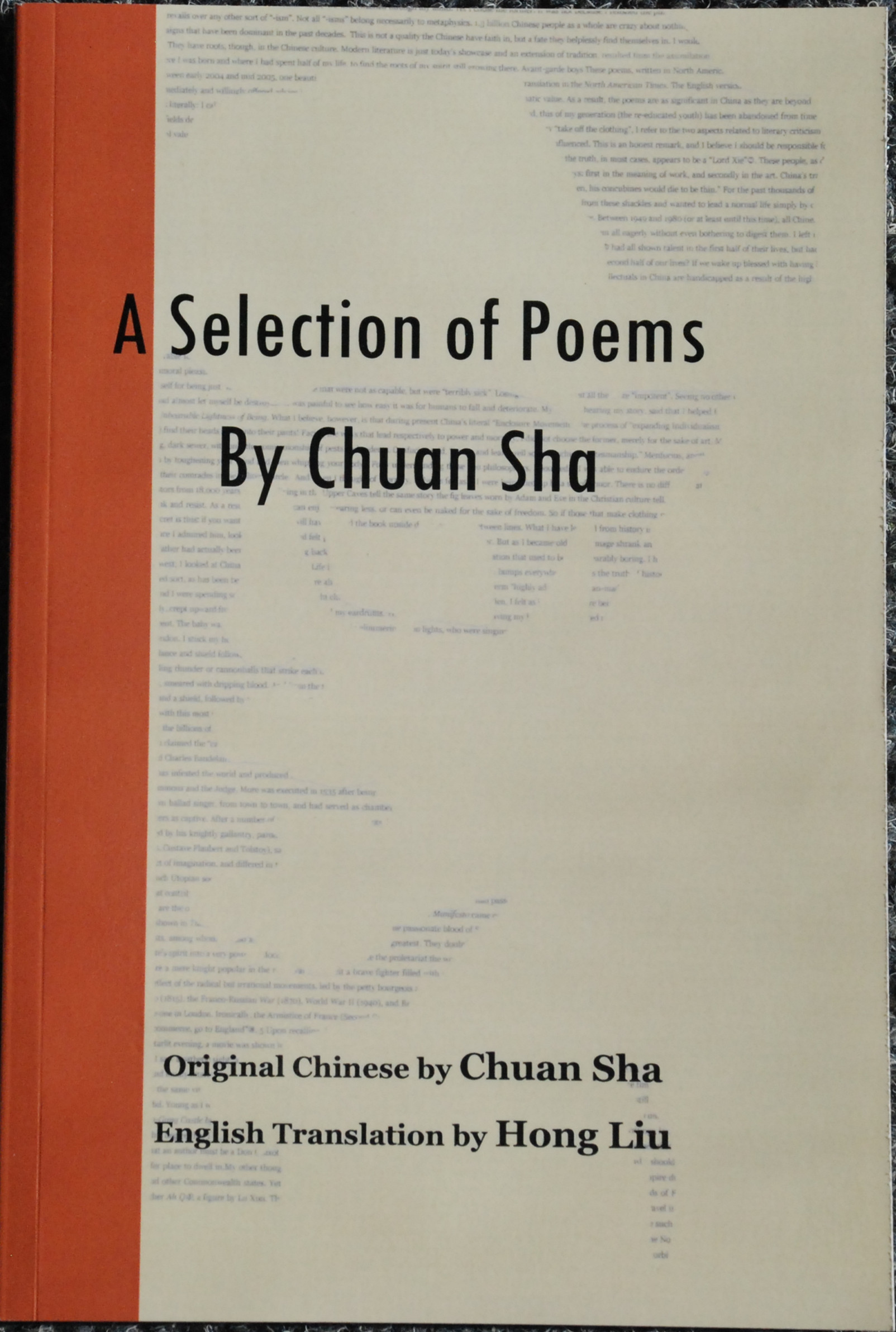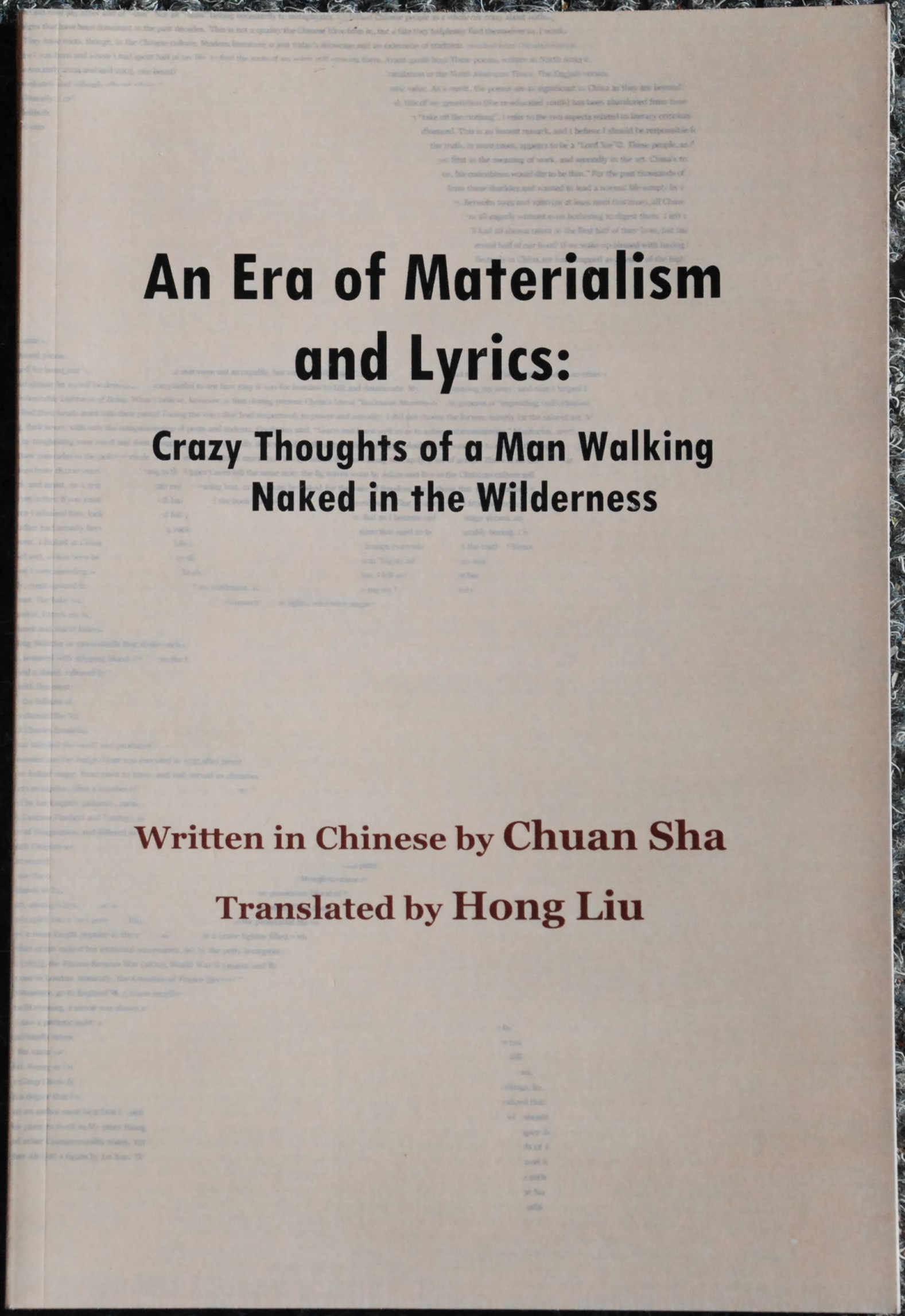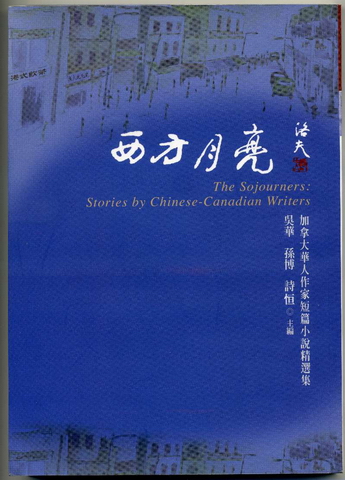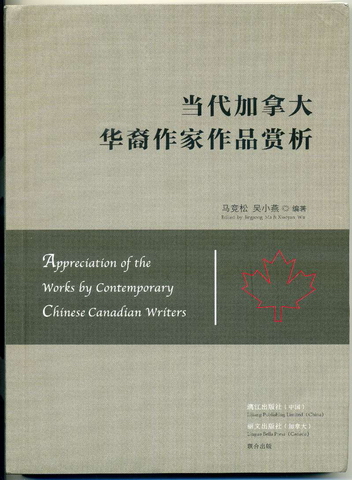(1)离 别
浅浅的离别
伴着晨雾暮霭的冥朦
在起航的锚链声中
火车闪光的双轨上
或是村头小路上溶进天边的黑点子里
更多的离别
在闪光
吼喊中
看见
听到
然而
一些离别
翻卷着隆隆的生的火焰的目光
随着铁门沉重铿镪的合拢而静寂
后来
石碑上苔藓覆盖的盲瞽的镌文
清明原野上点点紫花
向你述说
夜的终点
那边
那边
亲人的思念
原载川沙诗选集《春夜集》
Goodbye
Goodbye, light and quick
amidst murky morning mist or fog at dusk,
to the sound of ships ready to set sail,
along the shining rails under the train,
or in the small black dots disappearing into the sky
at the village entrance.
Goodbye,
in tears,
in cries,
seen,
or heard.
Goodbye,
roaring past the fiery eyes of life,
dying down as the iron gate closes,
then,
simply words carved on mossy tomb stones,
purple blossoms in the fields of Qingming,
telling you,
where the night ends,
there are people
who miss you.
[1-1]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痛
王 焱 博士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注定的,人的一生要经历许多的离别。所谓“多情自古伤离别”,“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面对人生的聚散无常,凡夫俗子总免不了忧郁伤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充溢着悲悯诗情的国度,易水诀别、霸王别姬、昭君出塞、诸葛出师……“离愁别绪”一直以来都是文人骚客反复吟咏渲染的主题。当时空的列车穿梭到现代,当日新月异的交通通讯工具以及传媒技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编织成一张便捷而又结实的网,我们依然发现,“离愁别恨”还是如此这般的不可承受。川沙先生的这首《离别》,以一种生命的景深感,对离别这一情愫的形蕴进行了梳理和勾勒。全诗分三节,递进地叙述了悲剧意蕴由浅入深的三种离别,凸显了离别中最为深重、最不可承受的悲剧性力量。整首诗凝练澄澈,圆润醇和,堪称佳作。
在川沙先生看来,同是离别,却演绎着不同的故事,怀揣着各异的伤情,有着不一样的浓淡深浅。其中,“浅浅的离别”便是最俗常理解的亲人朋友间的“生离”。川沙先生只用几句简短的诗行和一些日常的意象便把这种离别的况味勾画了出来:在某一个微冷的清晨,伴着晨雾暮霭的冥朦,有一位在“我”生命中具有非常意义的人,即将远行(在现代社会,若不是远行,是断用不着如此上心的)。斗转星移,古时的瘦马和兰舟已换作今日的航船和火车,“在起航的锚链声中”,或在“火车闪光的双轨上”,人意或者天意,小别或是永诀,他(或她)将离“我”而去。在这一节中,“或是村头小路上溶进天边的黑点子里”这一句诗写得犹为传神:在那的久远昏暗的“村头小路上”,送别的人一直凝视着远行者的或义无反顾或不住回首的身影,看着他的身影慢慢便小,直到成为黑点子溶进天边,这才恍惚回过神来,拾路归去。川沙先生用敏锐的触角把握住了送行者霎那间的心灵颤动,将那种依恋与不舍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出来。
而“更多的离别/在闪光/吼喊中/看见/听到”,“更多的离别”指的是什么,川沙先生语焉不详。我认为指的是“我”所目睹耳闻的他人的离别,这是相对于上一节的“我”所亲历的离别而言的。我所理解的“闪光”喻指离别的视觉见证(联想图式:闪光–闪光灯–照相机–照片–某种回忆,或者闪光–泪光–伤心的眼泪),是一种凄楚怀旧的氛围;而“吼喊”则喻指离别的听觉见证,是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囿于自我时空局限性,见证他人的离别总比自己亲历的离别要多,这是很好理解的。然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人的离愁别恨也同样能够触及到自我灵魂深处最柔软的地方。相比于上一节的客观意象的铺陈,悲伤的主体情绪已经在本节略带节制地显现出来。
在最后一节中,离别的悲痛被推向了高潮。诗人用“然而”二字起首,使得前两节层进式的文脉骤显跌宕,平缓的叙述节奏也骤显紧张,而这种叙述张力暗含着有一股强大的情感冲击力即将不可遏制的迸发出来。显然,诗中所写的“一些离别”便是阴阳两隔。“翻卷着隆隆的生的火焰的目光”是一种强烈的生的欲望,却被死亡–这扇沉重的铁门,在“铿镪的合拢”的瞬间,阻断。在死亡不可抗的强力下,一切鲜活的生命体都灰飞烟灭,归于“寂静”。死者已矣,留给亲人的是无尽的哀恸,只有寄托墓碑上镌写的文字,和清明时节上祭的鲜花,跨越阴阳的藩篱,驱逐彼岸世界夜一般黑暗的阴霾,述说亲人的思念。人常言,生离死别,肠断心摧。“生离”固然令人唏嘘惘然,但若与“死别”相比,“生离”终还是多可慰藉。因为“死别”因其绝对不可逆性,表现出最为深重的悲剧性内涵,是生命中最不可承受之痛。行文至此,我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时光的钟摆晃过了千余年,这种古老的情愫在川沙先生的诗行中找到了新的契合。
在这一节中,川沙先生纯熟的诗歌创作技法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石碑上苔藓覆盖的盲瞽的镌文”一句,通过对“苔藓”意象和“盲瞽的镌文”意象的突出,将伊人永绝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刻骨铭心之痛传达出来,含蓄而又淋漓。又如“夜的终点”一句,巧妙地将时间感“夜”和空间感“终点”熔结起来,意境深邃,又立体可感,与李商隐《嫦娥》中的“碧海青天夜夜心”有异曲同工之妙。
1-2 以“缺”求“全”:悲婉动人的离别之殇
江武义
听一位心理学专业的学长说:离愁别绪,从审美心理学上讲,是一种缺陷美。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理论,这种非常态的情感,在力的结构图式上呈现出的是一种不对称的“形”,他诱发出的是一种强烈的“完形”的审美冲动,与对称、和谐的“形”相较,这种由非常态情感生成的不对称的“形”具有更大的审美张力。也正因为如此,离愁别绪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历久不衰的主题。无数文人墨客,都曾和着血泪写下了许多以“缺”求“全”的悲婉动人的诗篇。
这首诗,一方面沿用了中国传统的离别母题,但是,另一方面,诗人又站在了当代的人文高度,赋予了传统母题时代的精神内涵。
诗人采用逐步深入的写法,由“浅浅的离别”到“更多的离别”,再到“一些离别(死别)”,短短的二十二行诗,把人一生中从生时短暂分离到死时的永诀诉说尽。看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实则是对人生的一种深度思索,引起无限回响。
第一节诗人定义的是“浅浅的离别”:时间是“冥朦的晨雾”或“暮霭”时分,地点是在“响着起航的锚链声”的码头,或者有着“闪光的双轨”的火车站,抑或“村头的小路”。离开的人是谁呢?是出去寻梦或是拓荒?离开的时间是否短暂,是否长久,是几天,几个月,或几年?……每个人都可以在此找到自己的身影。回忆起当时浅浅的愁绪,回忆起分离期间的思念,回忆起再聚首时亲情的点滴温存。这种离别,应是经常发生,我们已能承受,即使思念尽管是段走不完的路。但我们已能适应,并不会引起太多的情感风暴,这便是“浅浅的离别”。“晨雾暮霭”是“浅浅的离别”的见证,却也是常被人诉诸离愁别绪的美景。
第二节更是诗人语言的高度浓缩,把生离中除“浅浅的离别”之外的所有全部概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人世间生时的别离万万种,道不尽,说不清,然而有一些离别却是不像“浅浅的离别”那般单纯,可能多了些迫于无奈,或者其他难以言说的问题而逼不得已。这些离别在“闪光”和“吼喊”中发生的确实有大半。诗人巧妙地用“闪光”“吼喊”来概述这些离别,恰到好处,同时显得更能引人遐想。
前两节诗人以“起航的锚链声”、“火车闪光的双轨”、“村头小路”和“闪光”、“吼喊”五组意象分别概括了“浅浅的离别”和“更多的离别”这两种生时的别离,诗人只是淡淡的仿似旁观者的描述这两种离愁别绪,却引起读者无限的遐思和情感变化。
这两节的离别是根源于空间的阻隔,但这种空间阻隔终究在有生之年还可能得到弥补。而第三节的生死离别却不再是短暂的,而是永恒的。
“翻卷着隆隆的生的火焰的目光/随着铁门沉重铿镪的合拢而静寂”
生活便是如此。“隆隆的生的火焰”、“ 铁门沉重铿镪的合拢”两组修辞深刻表现了“极具顽强的生”进入“沉重的死”的令人痛彻心扉。“沉重的铁门”一旦“合拢”便不再开启,只能通过“石碑上苔藓覆盖的盲瞽的镌文/ 清明原野上点点紫花”来述说对生者的思念。生,死,一线之隔,一时之遥。茫茫相隔,需要以怎样的心境来面对?“死者长已矣!”诗人不说生者对死去之人的思念,却通过“镌文”、“紫花”以示死者在“夜的终点那边”对亲人的思念,与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更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生离死别,本是人生亘古不变的主题,然而诗人并不像传统般只是述说个人的离别愁绪,而是将个人的情思上升为论述人生的的一种永恒现象,思考人生,从而拓宽了诗主体的深度和广度。
这首诗也充分表现出了诗人在诗歌意象经营上的独具匠心。在表现离愁别绪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情绪、意念时,诗人没有选择传统的孤雁飞鸿、馆驿荒径等意象,而是择取了颇具现代色彩的“锚链声”、“火车站”、“村头”“闪光”、“吼喊”、“石碑上苔藓覆盖的盲瞽的镌文”、“紫花”等意象来寄予情感。这样,诗人就以独特新颖的意象作为抒情基点,从离愁别绪这种人们所普遍体验的感受中开掘出了自我独具的崭新感受,从而使在离愁别绪的边线领域上达到了发前人所未发现的较高的美学境界。在意象的安排和组接上,这首诗采取了意象并列的组合形式。诗歌围绕离愁别绪这一情感、意念进行联想与想象,产生出了“锚链声”、“火车站”、“村头”“闪光”、“吼喊”、“石碑上苔藓覆盖的盲瞽的镌文”、“紫花”这些意象。这几个意向的关系如在一棵树杆同时向外长出的一些新枝,形成并列式的意象结构。从情感抒发上看,这首诗的意象组合又有着由浅到深、由生到死这样延伸的顺序。表达出了绵绵的人生之思。
1-3深沉持久的痛
曲国铖
“浅浅的离别/伴着晨雾暮霭的冥朦/在起航的锚链声中/火车闪光的双轨上/或是村头小路上溶进天边的黑点字里……”这是本诗仅有三段中的第一段,开篇便渲染出一种黯淡忧伤的情感氛围:清晨的雾气白茫茫一片,朦朦胧胧之中,远方的所有都在眼前若隐若现,仿佛置身于仙境:或者在黄昏日落的时候,夕阳徘徊在大地边缘,将天边的云霭渲出一种壮丽的辉煌,整个世界仿佛都要随着太阳的西下而沉睡。就在此时,即将与亲人或挚友挥手告别,“再见”还未出口,热泪已盈盈欲坠。本有千言万语在心中,此时却一句也说不出口,只化作一个“珍重”,载着沉甸甸的思念和祝福,在互相理解的眼神中,给亲友以慰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之于王昌龄,会有什么样的祝愿与思念呢?晨雾固然飘渺若仙境,然而那份凄清,也给人以无尽的感伤;暮霭固然壮丽,然而那份凄美,也给人以悲凉和惆怅。常人尚且触景伤怀,又何况即将分离之人呢?船舶已开动,水手揉着惺忪的睡眼抛开起航的锚链,“哗啦啦”“哗啦啦”,更使人感到愁闷,感到生命时光的紧迫。火车的汽笛开始鸣响,悠长粗重而略带尖锐的声音,越来越短促,越来越急迫;车轮快速地在同一处铁轨上依次滚过,月光从轮间的间隙射进来,映着光滑的车轨,一闪一闪,仿佛在记录着历史,向人们展示时光是怎样一点一点地流淌,从指间,从眼前。村头的小路在关怀的目光中延伸,随着亲人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终消逝在苍天和地平线的交接处。那离别,浅浅的离别,就这样象远飞的雁群一样,渐渐地,渐渐地,溶进天边的黑点子里,再也看不到了。
“ 更多的离别/在闪光中/在吼喊中/看到/听到” –暂时的离别,带来暂时的伤痛。有些离别,在火车双轨的闪光中,在船舶离岸的锚链声中,在久经风霜的水手吼喊声中,被听到,被看到,被嗅到,被触摸到,被品尝到。咸得像盐,苦涩中混着无奈和不舍。然而离别只是暂时,在下一个轮回的火车双轨闪光中,船舶靠岸的锚链声中,勇敢水手吼喊声中,之前积累的思念之痛都被重逢的巨大喜悦所淹没。欣喜,除了欣喜还是欣喜,失去之后重又获得的欣喜。暂时的离别带来伤痛的暂时。这样的离别在当时使人感到疼痛,然而一旦过去,一旦与思念的人相聚,便马上成为快乐和温馨的回忆。这样的离别是生活的调味品,让那些“久处芝兰之室,而不觉其香”的人,让那些在幸福中感觉不到幸福的人,让那些因长久拥有而反不觉拥有之快乐的人,在失去的痛苦之后收获喜悦。这些人是上天的宠儿。
“然而 / 一些离别翻卷着隆隆的生的火焰的目光 / 随着铁门沉重铿锵的合拢而静寂 / 后来 / 石碑上苔藓覆盖的盲瞽的镌文 / 清明原野上的点点紫花 / 向你诉说 / 夜的终点 / 那边 / 那边 / 亲人的思念……”–诚然,有暂时的离别,便有永远的离别,这便是死亡。人即使可能抗拒一切,也不能抗拒死亡。石碑内外,阴阳两隔,碑面上苔藓覆盖的盲瞽的镌文,不过是冰冷的文字;清明原野上的点点紫花,或许能够讲述墓中埋藏的是曾经一个多么鲜活的生命,一程多么传奇的人生旅途,一段多么深厚的情感历程。死者已矣,生者却必须承受离别的痛苦,直到自己也被死神带走。杨过十六年苦苦守侯,终得与小龙女相会。与那一刻相比,再大的付出又算得了什么呢?假如小龙女果真已死,杨过又该当如何呢?离别之苦如此深重,所以断肠崖上,神雕大侠纵身赴死。而杨过终究是幸运的,金庸先生笔下留情,让他痛苦了十六年,然后重逢小龙女,快快乐乐地共度余生。萧峰却注定做一个悲剧英雄,在最辉煌的时刻,突然得知自己契丹人的身世,从此人人喊打,从人生的颠峰一下子落至痛苦的低谷。唯一的红颜知己阿朱,又被自己一掌震死。人生最痛之事,莫过于亲手将自己的最爱毁掉。任你武功卓绝,聪明绝顶,于死亡这件事上又能做些什么呢?疾病可医,破镜可圆,惟有死亡,带给人类最大的无奈。有圣人说,为人须心怀天下,不可儿女情长。然而,人是感情动物,毕竟,世间绝大多数是凡人。关心爱护自己的人,始终有限;自己所深爱依靠的,也终不过几个人。倘若自己所深爱的人永远离去,那么一个人将靠什么支撑自己活下去呢?那种旷世的孤独,如何躲避?那种越思越痛的往事,如何冲洗?这样的人生,不是太无味了吗?
也许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走到人生的那一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假如有一天,自己的慈父爱母辞世,习惯于父母呵护的你该如何?假如有一天,所有亲人朋友都离去,留下自己孤苦伶仃,你又该如何?这并非痴人说梦话,毕竟,死亡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我们要意识到,不可能做到永远拥有,要学会珍惜。很多人失去之后,才后悔自己的无知,才知道应该去珍惜,然而噬脐莫及,能做的只有追思。一丝一毫,一点一滴,一个灿烂的笑容,一个理解的眼神,一个善意的提醒,均须珍惜。幸福就在身边,平平淡淡才是真。既然分离是必然,那么在分离之前好好珍重是最重要的事情,分离之后也不必感到痛苦了。做不到心怀天下悬壶济世,做到心胸旷达,拿得起放得下还是可以的。上天赐给我们生命,不能只用来思念伤神,应该做些有用的事情。人活着,积极一点总比消极好。亲人逝去,思念必不可免,然而不能让它占据生活的主旋律。
“石碑上苔藓覆盖的盲瞽的镌文/清明原野上的点点紫花/向你诉说/夜的终点/
那边/那边/亲人的思念……”
失去世上最亲最爱之人,其痛可知;思念最亲最爱之人,其哀可知。但是痛苦和思念之后,还是要抖擞精神。睁开眼睛,明天又是崭新的一页。
1-4 生离死别:柳和长亭的新诗表达
白丽
“离别”,自古到今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关于离别的诗作、文章、影像、乐曲多得数不胜数,也许是因为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总是离别多于相聚吧。
在中国,离别一般以柳为赠礼,渐渐地柳成为了离别的代名词。如岑参在《送韩巽入都觐省便赴举》中写到“槐叶苍苍柳叶黄,秋高八月天欲霜。青门百壶送韩侯,白云千里连嵩丘。北堂倚门望君忆,东归扇枕后秋色。洛阳才子能几人,明年桂枝是君得。”又如宋代的柳永在其《雨霖铃》中写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晚风残月”。在以上两首作品中,全文未出现一个离别的字眼,均是以柳言别。除了柳,长亭也是离别的象征,“长亭连短亭”,一程又一程的送别,然天下无不散之宴席,该离开的总归会离去。柳和长亭便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离别的代名词。
当然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其它的送别形式,如当荆柯奉命去刺杀秦王时,友人为他抚琴吟歌送别,唱响千古名句“风飘飘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样的离别也许应该是一种悲壮吧,明明知道是一去不复返,却须一步不回地离开。
在现代与时俱进的背景中,中国的居民不会再去折柳送别,也不会一程又一程地去送别即将离开的人。最多只是送上离别的车子,然后站在月台上,流着不忍分离的泪水,重重的挥起双臂,久久不让它落下,于是“月台”成了新一轮的离别代名词。
然而,川沙先生此首《离别》却是将离别之痛寄予于晨雾暮霭、锚链、火车的双轨、村头的小路上、溶进天边的黑点子以及闪光、吼喊、铁门之中,更有那别后重逢于墓前之景之痛中。
起句“浅浅的离别”,乍看之下是在晨雾暮霭中的浅浅的、淡淡的一种心情,离别的难舍之情看似若有若无,但在诵读之间,若慢慢体会便可深深体会到在这文字间透露出的是似海一般深、似天一般广的不舍之情。
这种情愫伴着晨雾暮霭的冥朦溶进了天边的黑点子里,同时也溶进了诗人的心中。
光亮的双轨上飞驰的火车毫不留情地带走了亲人亦或是带走了诗人自己,迷朦的空气中滞留的是离别时总也说不完的叮咛和担忧,再由呼吸深深地印刻在心底,氤氲成深深的思念,驻进分离两地的人儿的心房,辗转成为对相聚时刻的期盼。
但是,不忍离别之心再重也有必须离别的时候,欢聚的渴望在现实的残忍下也被无情的沉重的铁门那铿锵的合拢隔离出尘,剩下的是在静寂的世界中孤单一个人行走,以及对亲人时时的思念。
不过,还好,只要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总有希望再见。哪怕这一天遥远地任凭我们使尽所有力气也无法触及,但它在遥远的前方等待着我们的归去,指引着我们向它进发,支撑我们向它走去,使我们不会倒下,不会迷茫。
然而,最痛的也许是那一别成永别的无奈。远在异乡时思亲的情素支撑起自己,让自己一直沿着自己正在走的路勇敢地走下去,却不想归来时亲人却已逝去,可见的只有点缀着点点紫色的野花的坟墓以及墓前那苔藓满布的石碑上镌刻的盲瞽的碑文。离家已久,思念已深,日夜期盼的便是与亲人团聚时诉说自己的思念,不想却在归来时无人可诉,唯一可做的便是从盲瞽的碑文中去寻找以及告知他乡与故里之间深夜寂静时彼此的深切思念。这是怎样的哀伤啊!
不明白的我们便变得失望了。失望的人儿也许会哭泣,也许会沉沦,也许会堕落,也许会绝望到连哭泣的力气也没有,也许也会像诗人川沙一样,将离别的痛在纸笔间宣泄,将离别的苦汇聚成歌一样的诗,也许……也许会发生好多好多不同的情况,但是相同的一定是那埋藏在心底亦或是流露在外的那深沉的哀伤与失去亲人的痛吧。
诗人川沙远离故土,对家乡故里以及留在家乡故里的亲人的思念一定深沉得不可估测,否则如何能知晓生离死别的哀伤呢,又怎么能够将这样深重的哀伤揉进字里行间呢?
生离和死别,一样是别离,却是不一样的别离。生离,起码还有再见的机会,有时虽然机会渺茫,但是总有一线的希望存在;死别却是真正的再见——再也无法相见,不是不想,而是不能。阴阳两地的距离,不是一道沟渠,不是一潭湖水,不是一座高山,也不是一片汪洋,那是有与无的距离,是我们无法横越的距离。我们无法穿越生与死的阻隔,我们只能在生的一地缅怀生的记忆,幻想死的世界。
离别,让我们哀伤,让我们痛苦,也许也让我们后悔,让我们永远离开自己思念的人……
我不了解川沙先生是否有着相同的经历,但他的内心一定也有着类似的哀伤吧,最起码在写下此诗篇之时内心有着那深深的哀伤吧。否则他如何能写下这感人肺腑的诗篇呢?
读着充满离别哀愁的文字,想起此时此刻我亦不在亲人身边,便也觉得心中满是思念和哀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