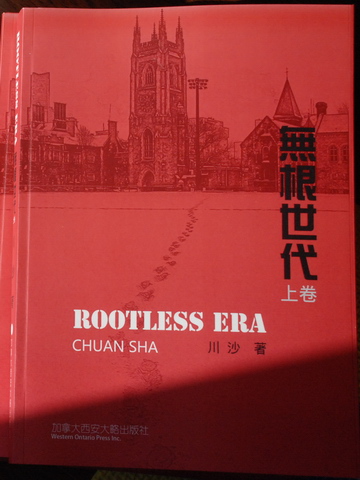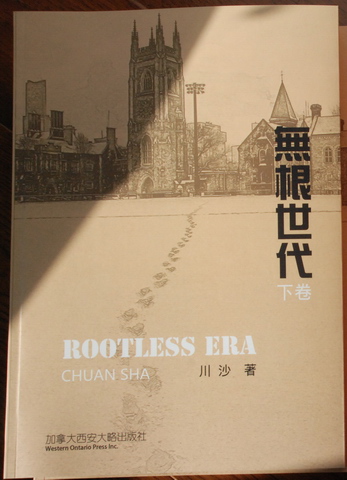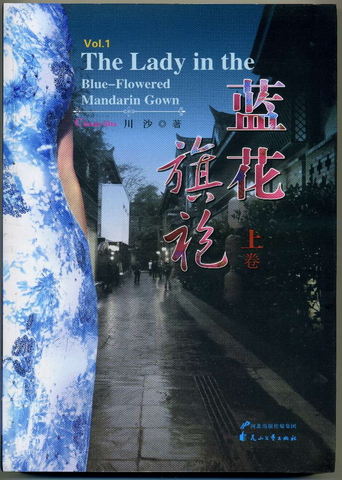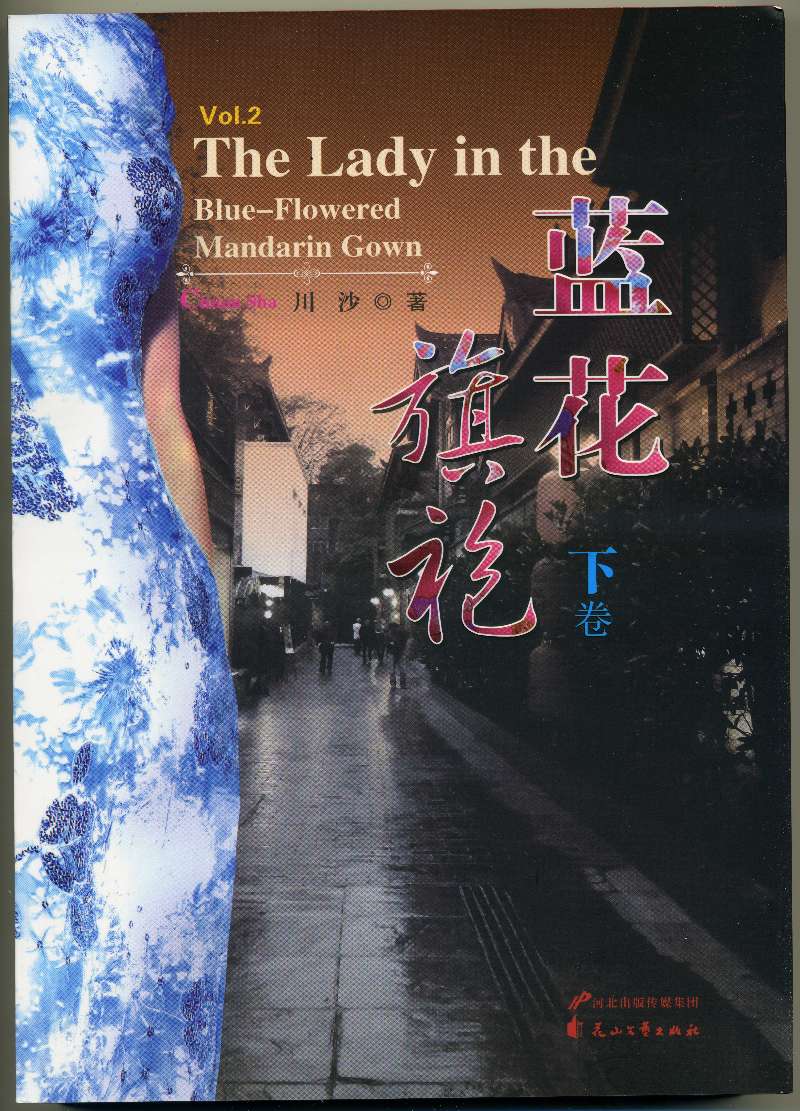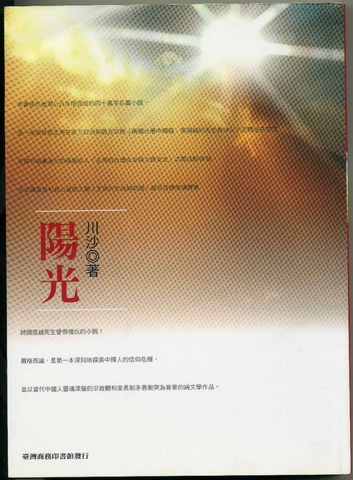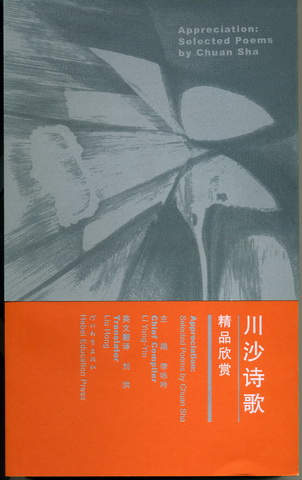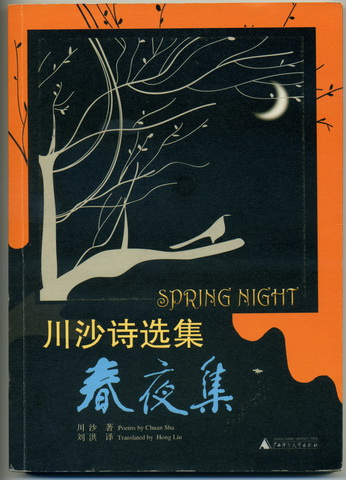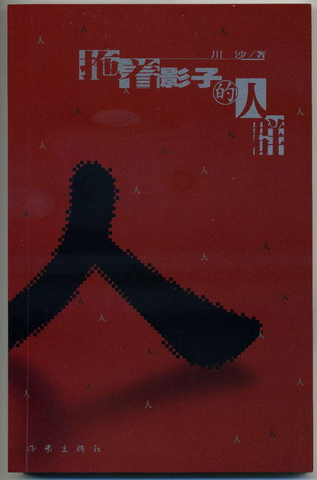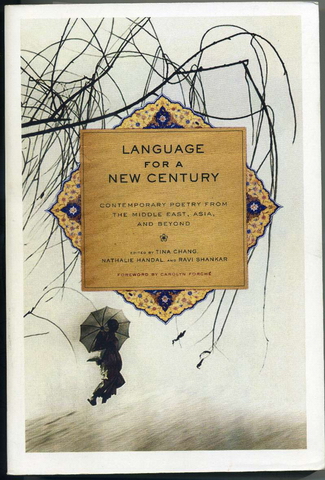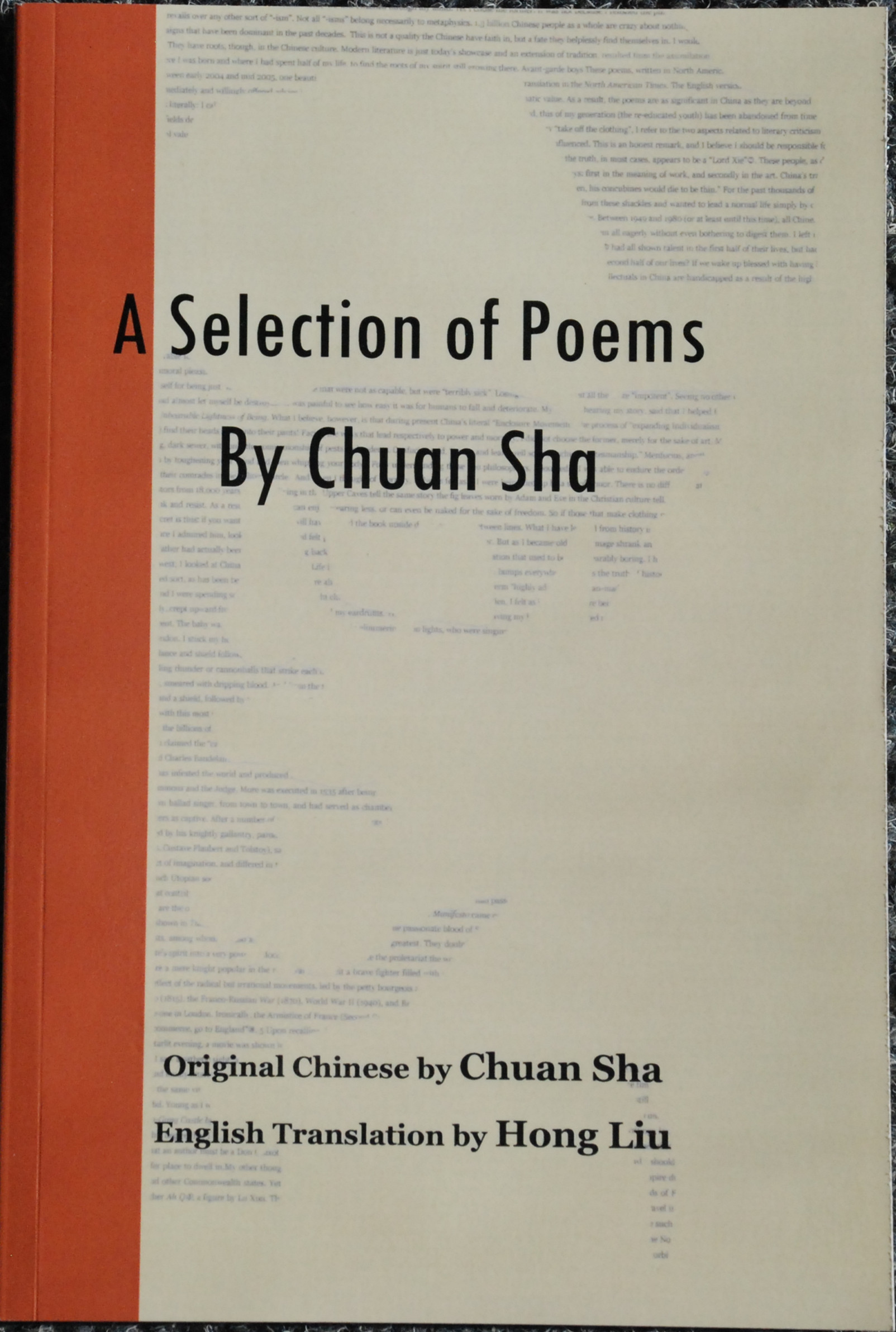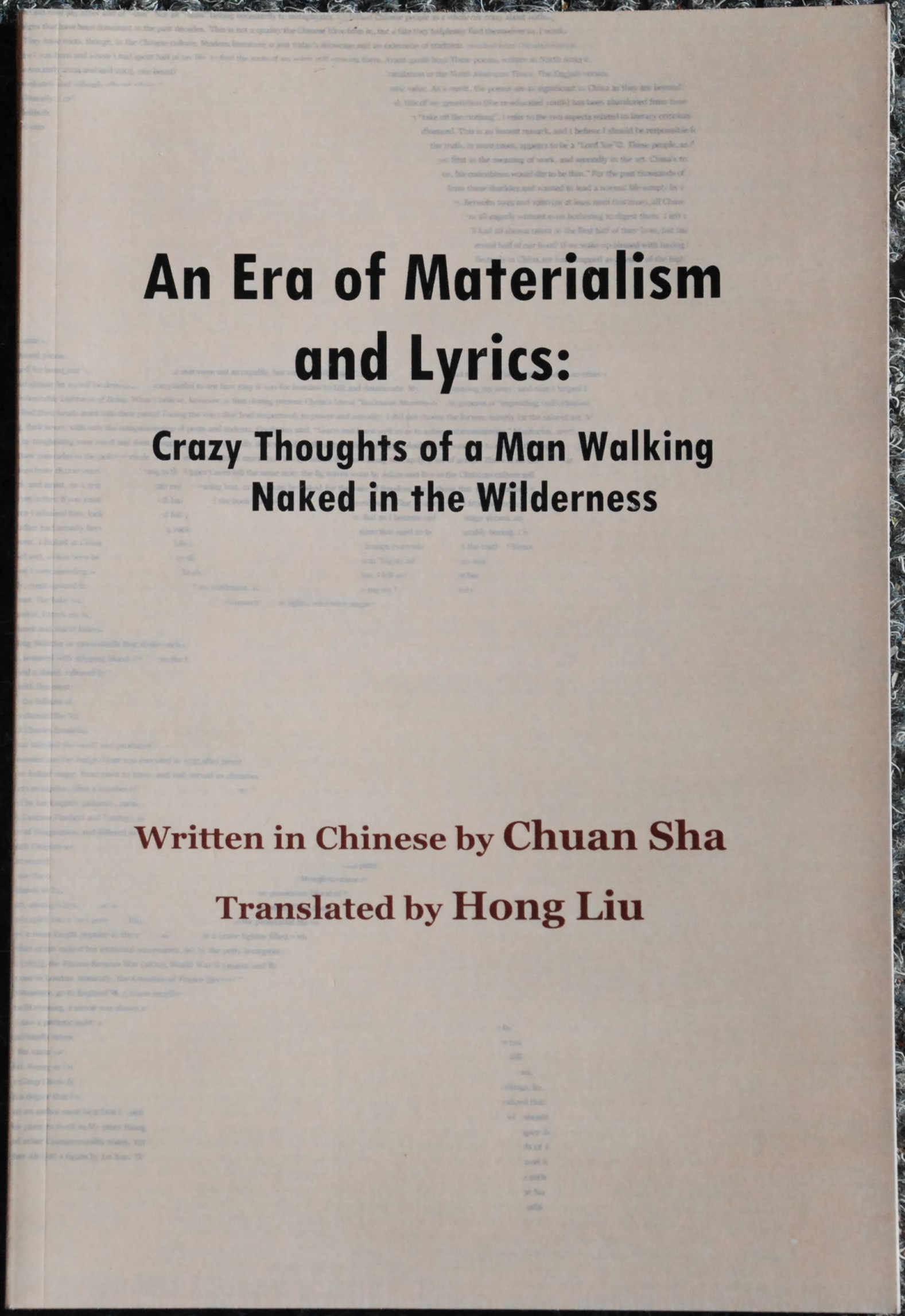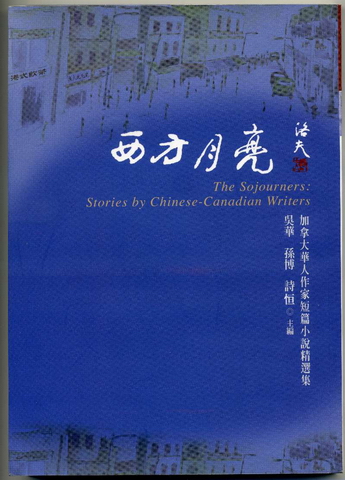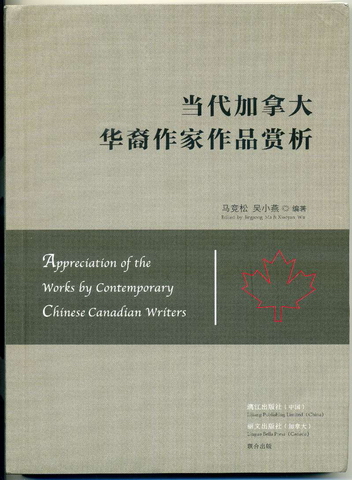(35)诗人永远在栅栏里
诗人永远在栅栏里
诗人永远在草坪那边的木板栅栏里
诗人的目光
诗人的目光穿过窗外灰色的木板栅栏
穿过木板栅栏前面的夹竹桃林
他的目光穿过那些缝隙看外面喧闹的天空
他看那些能够长大的小孩
日日月月年年
他看那些小孩长成大人
看他们渡过远处的河流
他看太阳出来又落下
看月亮出来又落下
他听教堂的钟声叮叮当当响亮
他看他们在河对岸的集镇上和
背枪的猎人
提秤杆的商人
戴眼镜的当铺掌柜
他看他们在欢快做事
做那些
他不懂的
不喜欢的
害怕的事情
诗人长大了
诗人的身体长大了
诗人的心永远在阁楼里
诗人永远在栅栏里
诗人永远在阁楼顶上的书本里看
看木板栅栏外面远处的世界
他从阁楼顶上发黄的布面精装书的插图里看
看他前面的诗人们
都一个个从阁楼顶上的窗口看世界
他看
那些长大的他们在河对岸的集镇上和
背枪的猎人
提秤杆的商人
戴眼镜的当铺掌柜
他看他们在欢快做事
35) Poet inside the Fence
The poet is inside the fence, forever
And forever he is inside the fence beyond the lawn
The poet’s gaze
The poet’s gaze reaches the gray wooden fence outside the window
Then the bamboo and peach bushes in front of the fence
Through the gaps he looks up into the noisy sky
And at the children who will surely grow up
With each passing day, or month, or year
He will see them grow up and see them
Cross the river far away
He sees the sun rise and set in
And the moon appear and disappear
He listens to the church bell ringing
While on the river’s other side the town market comes to life
The hunters with rifles
The businessmen with scales
The pawn shop owner with a pair glasses
He sees them busy with joy
Doing all that
He does not understand
Does not like at all
And is afraid of
The poet has grown up
Physically, yet his heart is locked
In the attic forever
The poet is inside the fence forever
And forever he stays in the attic reading
And looking at the world beyond the fence
He reads the faded colored clothed books and the pictures
That he finds in the attic, and he sees the poets before him
Looking too at the world from the attic
He sees those who grow up
And busy themselves in the marke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The hunters with rifles
The businessmen with scales
The boss with glasses on
Excited, busy, and happy
[35]被选中的一个
王嘉军 硕士
本雅明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可技术复制时代中,艺术所缺乏的是”氛围“,这种氛围指的是”一定距离外的独一无二的显现–无论它有多近。夏日午后,悠闲地观察地平线上的山峦起伏或一根洒下绿荫的树枝–这便是呼吁这些山和这一树枝的氛围“。诗歌,作为文学之桂冠,作为亚理士多德口中艺术的代名词,它的诞生也无疑是在这样的氛围造就的,而诗人,无论是天性使然或者有意警戒,一直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世界的距离。
“他看他们在河对岸的集镇上和/背枪的猎人/提秤杆的商人/戴眼镜的当铺掌柜/他看他们在欢快做事”。河对岸的集镇是世俗生活的象征,而“背枪的猎人/提秤杆的商人/戴眼镜的当铺掌柜”这些人就是在这幅浮世绘中出现的各种角色,他们在欢快做事,做的是什么事呢?“枪”、“秤杆”这些意象已经暗示了他们所在做的是生活的算计与利益的争夺,“戴眼镜的当铺掌柜”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鲁镇,那是一个典型的“河对岸的集镇”的代表,里面有鲁四爷、有闰土、有“豆腐西施”、有祥林嫂,尔虞我诈,世态炎凉。这个时候,我还想起了《孔乙己》中故事的复述者,那个垫起脚板才能够到柜台的小掌柜,他也像极了一个栅栏后面的诗人,向读者讲述着他所看到的一切:孔乙己的迂腐与善良,周遭人们的愚昧与无情……而这一切,在别人看来都是稀松平常,合情合理的。人们都在欢快做事,如此欢快,以致麻木。只有栅栏后面的诗人会为这一切而置疑,而动情。
诗人就是这样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川沙说“诗人长大了/诗人的身体长大了/诗人的心永远在阁楼里”,诗人的心永远像新鲜的果肉,保持着降临之初的纯洁状态,不会被尘土遮蔽,也只有这样,它才能对外部的一切保持着敏感,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的解读是谨慎并且表层的,在此之前,也曾有人发过这样的感叹:“艺术家是长不大的孩子”,我认为川沙的诗更深沉之处在于它已经超越了这一层感叹之外。栅栏的原初功能是卫护,卫护牧场里的牛羊或者花园里的草木,然而,它也可能是一种桎梏,正是它限制了牛羊的奔跑和草木的滋长。在空间上,栅栏将世界二分,从此世界上只有栅栏这边和栅栏那边的区别,然而,我们现在想要问的是诗人和凡人,到底哪个是关在栅栏里的人?外面的世界纵使宽阔,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不也正是在栅栏的里边么?进一步的追问是诗人寄寓的世界到底是更狭窄还是更宽阔?对于这一切,诗歌没有给出回答,当我们用心灵去接触这个问题时,我们朝天仰望,是否也看到了草坪那边的木板栅栏?
诗人与凡人的关系如此,诗人与诗人的关系又是怎样呢?“诗人永远在阁楼顶上的书本里看/看木板栅栏外面远处的世界/他从阁楼顶上发黄的布面精装书的插图里看/看他前面的诗人们/都一个个从阁楼顶上的窗口看世界”,诗人与诗人,他们在阁楼中仰望,看见前面的诗人,前面的诗人又看见前面的诗人……像一副多米诺骨牌,彼此传递,声声不息。在栅栏里的诗人是孤独的,孤独的另一个意味是独立,正是这种孤独造就了他们,而所有诗人共同的孤独汇聚在一起,就足以形成另一种风景,另一种力量。这力量使他们感受到彼此的存在,像辽远的夜空中,一颗星星感受到另一颗星星的跳动。
诗中的最后一段,又回复到诗人对那个河对岸的集镇上的人们的观望,太阳升起又落下,那些能够长大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他们也无可挽回地融入到这副浮世绘中。新的一天来临,地上的人们还在做着他们的差事,乐此不彼,诗人注视着栅栏那边的世界。这一段的文字与上面段落中所出现基本相同,却由于整首诗的行进而延伸出了新的意涵,略带讽刺,更多的却是悲悯。
我后来从作者川沙处得知,这首诗的缘起是1995年秋天诗人在爱丁堡的一座图书馆里看见瑞士象征主义画家费迪南德.赫德勒( Ferdinand Hodler 1853-1918)的画作《被选中的一个》( The Chosen One 1893-1894 ),受到强烈震撼后所作。笔者有幸也欣赏到了这幅画作,画中有连绵的绿地和山坡,展现出春天的生机,近景中一个光着身子的少年跪在一株正待发芽的小树前面,在少年和小树的周围,站立着六个圣母玛丽亚般的女人,她们身着浅绿色的连衣裙,手持蔷薇,肩上长着天使的双翼。她们每个人的面目不尽相同,但神色却很相像,似在沉睡,又似在安详地注视着那个跪在地上的少年。而那少年也把头抬起来,用好奇而又虔诚的眼神看着周遭的一切。
这观望的眼神又把我带回到诗歌中,此时,我想起了川沙的另一首诗《摆渡人》:“摆渡人/摆渡/在乡野之河/日出日落/摆渡/把众生摆渡/成河/在/生死悲欢/几劫几世之河/摆/渡”同样的日出日落,同样的静穆姿态,面对尘世纷扰,摆渡人和诗人都选择了一定程度的与世隔绝,摆渡人在冥河上划动双桨,诗人在栅栏边安静观望,这二者是否有共通之处?摆渡人摆渡众生的生死悲欢,摆渡众生到达彼岸,而诗人呢,是否也情愿躲在栅栏里囚禁自己,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观望来实施另一种救赎?而当将众生救赎完成之后,诗人又将如何,他将去向哪里?这首诗的题目彻底而坚决地告诉我们——诗人永远在栅栏里。